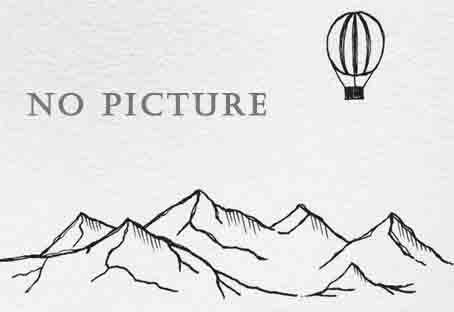第一篇:捡树叶的母亲 深秋的夜晚格外宁静,晚饭后,我和母亲一起出门散步。 秋风骤起,枯叶簌簌而落。路上铺满了黄色的叶子,走上去感觉脚底软软的,很舒服。母亲看到满地的枯叶,脸上露出笑容,居然兴奋地对我说 :“看到这些树叶,真想捡啊!”我奇怪地问:“为什么呢?捡树叶干什么?”母亲说:“前几日我做了一个梦,梦到去树林里捡树叶,看到满地的树叶,好高兴啊!” 看见我询问的神情,母亲陷入了回忆,给我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。 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,有兄弟姐妹五个,母亲排行老三。每天天还没亮时,母亲就起床去村边的树林里捡树叶树枝,这是去收集全家这一整天用来生火做饭的柴火。最难熬的是冬天,雨雪天气多,但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、出门干活的外祖父能在临行前喝上一口热汤,仍然风雨无阻地去捡树叶。每当在冰天雪地发现一丛干草或干树叶时,母亲就像发现宝贝一样欢天喜地。 母亲经常说,自己就是个受累的命,结婚前每日在田间劳作,结婚后为了盖房子养孩子,更是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辛劳度日。甚至在我出生前的十几个小时,母亲还拖着臃肿的身子,在田地里辛苦地采棉花。 如今家庭条件改善许多,母亲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,这都是往日的苦日子让她养成的习惯,她知道生活的不易,所以从不奢侈浪费。 我随手捡起一片枯叶,遥想着旧时的那个少女捡起它时的快乐模样,心中有酸楚,也有温暖。 母亲曾温暖着一家人的生活,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,轮到我温暖您了,请您紧握我的手,让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日子。第二篇: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,只养活了我一个。那一年,农村闹瘟疫,一个月里,她死了三个孩子。爷爷对母亲说:“心里想不开,人就会疯。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!”后来,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,并常对家里人说:“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,你们不要管我。” 麦秋两季,母亲疯了似的劳动,每天鸡叫就到地里去,收割、打场,很晚才回到家里。她的身上都是土,头发上都是柴草,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。她的口号是:“争秋夺麦!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!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。”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。母亲把馍馍晾干了,再碾碎煮成糊喂我。我多病,每逢生病,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,祷告过往的神灵。母亲对人说:“我这个孩子,是不会孝顺的,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。” 家境小康以后,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之人,尽力周济。有两个远村的尼姑,每年麦秋收成后,总到我们家化缘。母亲除了给她们很多粮食,还常留她们食宿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,长得眉清目秀,冬天住在我家,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,夜里叫得很好听,我很想要。第二天清早,母亲告诉她,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。 一年春天,我从远方回来。母亲高兴得不知给我什么好。家里有一棵月季,父亲养了一春天,刚开了一朵大花,她折下就送给我了。父亲很心痛,母亲笑着说:“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,今天忽然开了呢,因为我的儿子回来,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!” 一九五六年,我在天津得了大病,要到外地去疗养。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,当我走出屋来,她站在廊子里,对我说:“别人病了往家里走,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!”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。我在外养病期间,母亲去世了,享年八十四岁。 蒋妍摘自《孙犁散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第三篇:我的母亲 位于台中市大度山坡上的东海大学的右界,与一批穷老百姓隔着一条乾溪。从乾溪的对岸,经常进入到东海校园的,除了一群穷孩子以外,还有一位老婆婆,身材瘦小,皱纹满面,头上披着半麻半白的头发。清早进来,捡被人抛弃掉的破烂。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。第一次偶然相遇,使我蓦然一惊,不觉用眼向她注视;她却很自然地把一只手抬一抬,向我打招呼,我心里更感到一阵难过。以后每遇到一次,心里就难过一次。有一天忍不住向我的妻说:“三四十年来,我每遇见一个穷苦的婆婆时,便想到自己的母亲。却没有像现在所经常遇见的这位捡破烂的婆婆,她的神情仿佛有点和母亲相像,虽然母亲不曾捡过破烂。你清好一包不穿的衣服,找着机会送给她,借以减少我遇见她时所引起的内心痛苦。” 现在我一个人客居香港,旧历年的除夕,离着我的生日只有三天。不在这一比较寂静的时间,把我对自己母亲的记忆记一点出来,恐怕散在天南地北的自己的儿女,再不容易有机会了解自己生命所自来的根生土长的家庭,是怎么一回事。但现在所能记忆的,已经模糊到不及百分之一二了。 一 浠水县的徐姓,大概是在元末明初从江西搬来的。统计有清一代,全县共有二百八十多名举人,我们这一姓,便占了八十几个。我们这一支,又分为军、民两分(读入声),这大概是由明代的屯卫制而来。在界河的徐姓是民分,而我们则是军分。 军分的祖先便是“琂”祖。村子的老人们都传说,他是赤手成家,变成了大地主的人。因为太有钱,所以房子起得非常讲究,房子左右两边,还做有“八”字形的两个斜面照墙,这是当时老百姓不应当有的,因此曾吃过一场官司。 琂祖死后,便葬在后面山上。在风水家的口中,说山形像凤,所以我们的村子便称为凤形塆。琂祖有六个儿子,乡下称为“六房”,我们是属于第六房的。 大概在曾祖父的时候,由地主而没落下来,生活开始困难。祖父弟兄三人,伯祖读书是贡生,我的祖父和叔祖种田。祖父生子二人,我的父亲居长,读书,叔父种田。伯祖生三子,大伯读书,二伯和六叔种田。叔祖生二子,都种田。若以共产党所定的标准说,我们都应算是中农。但在一连四个村子,共约七八十户人家中,他们几乎都赶不上我们;因为他们有的是佃户,种出一百斤稻子,地主要收去六十斤到七十斤,大抵新地主较老地主更为残刻;有的连佃田也没有。在我记忆中,横直二三十里地方的人民,除了几家大小地主外,富农、中农占十分之一二,其余都是一年不能吃饱几个月的穷苦农民。 二 我母亲姓杨,娘家在离我家约十华里的杨家塆,塆子比我们大;但除一两家外,都是穷困的佃户。据母亲告诉我,外婆是“远乡人”,洪、杨破南京时,躲在水沟里,士兵用矛向沟里搜索,颈碰着矛子穿了一个洞,幸而不死,辗转逃难到杨家塆,和外公结了婚,生有四子二女;我母亲在兄弟姊妹行,通计是第二,在姊妹行单计是老大。我稍能记事的时候,早已没有外婆外公。四个舅父中,除三舅父出继,可称富农外,大舅二舅都是忠厚穷苦的佃农。小舅出外佣工,有很长一段时间,在下巴河闻姓大地主(闻一多弟兄们家里)家中当厨子。当时大地主家里所给工人的工钱,比社会上一般的工钱还要低,因为工人吃的伙食比较好些。 母亲生于同治八年,大我父亲两岁。婚后生三男二女:大姐缉熙,后来嫁给“姚儿坳”的姚家。大哥纪常,种田,以胃癌死于民国三十五年。细姐在十五六岁时夭折,弟弟孚观读书无成,改在家里种田。 三 父亲读书非常用功,20岁左右,因肺病而吐血,吐得很厉害;幸亏祖母的调护,得以不死。父亲一直在乡下教蒙馆,收入非常微薄。家中三十石田(我们乡间,能收稻子一百斤的,便称为一石),全靠叔父耕种,勉强维持最低生活。所以母亲结婚后,除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外,弄饭、养猪等不待说,还要以“纺线子”为副业,工作非常辛苦。她的性情耿直而忠厚。我生下后,样子长得很难看,鼻孔向上,即使不会看相的人,也知道这是一种穷相;据说,父亲开始不大喜欢我。加以自小爱哭爱赌气,很少过一般小孩子欢天喜地的日子。 到了十几岁时,二妈曾和我聊天:“你现在读书很乖,但小时太吵人了。你妈妈整天忙进忙出的,你总是一面哭,一面吊住妈妈上褂的衣角儿,也随着吊出吊进,把你妈妈的上褂角儿都吊坏了。我们在侧面看不过眼,和她说,这样的孩子也舍不得打一顿?但你妈总是站住摸摸你的头,依然不肯打。”真的,在我的记忆里,只挨过父亲的狠打,却从来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。 后来,叔父和父亲分了家。叔父分十五石田和一点可以种棉花的旱地,自种自吃,加上过继的弟弟,生活当然比未分时过得好。但我们这一家六口,姐姐十三四岁,哥哥十一二岁,细姐十岁左右,我五六岁。父亲“高了脚”,不能下田;妈妈和姐姐的脚,包得像圆锥子样,更不能下田;哥哥开始学“庄稼”,但只能当助手;我只能上山去砍点柴,有时放放牛,但牛是与他人合伙养的。所以这样一点田,每年非要请半工或月工,便耕种不出。年成好,一年收一千五百斤稻子,做成七百五十斤米,每年只能吃到十二月过年的时候;一过了年,便凭父亲教蒙馆的一点“学钱”,四处托人情买米。 学钱除了应付家里各种差使和零用外,只够买两个多月的粮食,所以要接上四月大麦成熟,总还差一个多月。大麦成熟后,抢着雇人插秧,不能不把大麦糊给雇来的人吃。大麦吃完后,接着吃小麦;小麦吃完后要接上早稻成熟,中间也要缺一个月左右的粮;这便靠母亲和大姐起五更睡半夜的“纺线子”,哥哥拿到离家八里的黄泥嘴小镇市去卖。在一个完全停滞而没落的社会中,农民想用劳力换回一点养命钱,那种艰难的情形,不是现在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。大姐能干,好强,不愿家中露出穷相,工作得更是拼命。 四 村落四围是山,柴火应当不成问题。但不是因我家没有山,所以缺柴火,而是因为一连几个村子,都是穷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数,种树固然想不到,连自然生长的杂木,也不断被穷孩子偷得干干净净。大家不要的,只有长成一堆一堆的“狗儿刺”及其他带刺的藤状小灌木。家里不仅经常断米,也经常断柴。母亲没有办法,便常常临时拿着刀子找这类的东西,砍回来应急;砍一次,手上就带一次血。烧起来因为刚砍下是湿的,所以半天烧不着,湿烟熏得母亲的眼泪直流。一直到后来买了两块山,我和父亲在山上种下些松树苗,才慢慢解决了烧的问题。分得的一点地,是用来种棉花和长豆角的。夏天开始摘长豆角,接上秋天捡棉花,都由母亲包办。有时我也想跟着去,母亲说“你做不了什么,反而讨厌”,不准我去。现在回想起来,在夏、秋的烈日下,闷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间,母亲是怕我受不了。我们常常望到母亲肩上背着一满篮的豆角和棉花,弯着背,用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,笃笃地走回来;走到大门口,把肩上的篮子向门蹬上一放,坐在大门口的一块踏脚石上,上褂汗得透湿,脸上一粒一粒的汗珠还继续流。当我们围上去时还笑嘻嘻地摸着我们的头,捡几条好的豆角给我们生吃。在我的记忆中,只有当我发脾气,大吵大闹,因而挨父亲一顿狠打时,母亲才向父亲生过气,却不曾因为这种生活而出过怨言,生过气。她生性乐观,似乎也从不曾为这种生活而发过愁。 五 辛亥革命那一年,我开始从父亲发蒙读书,父亲这年设馆在离家三里的白洋河东岳庙里。在发蒙以前,父亲看到我做事比同年的小孩子认真,例如一群孩子上山砍柴(实际是冬天砍枯了的茅草),大家总是先玩够了,再动手。我却心里挂着母亲,一股正经地砍;多了拿不动,便送给其他的孩子。放牛绝不让牛吃他人的一口禾稼,总要为牛找出一些好草来。又发现我有读书的天资,旁的孩子读《三字经》,背不上,我不知什么时候听了,一个字也不认识地代旁的孩子背。所以渐渐疼我起来。 这年三月,不知为什么,怎样也买不到米,结果买了两斗豌豆,一直煎豌豆汤当饭吃,走到路上,肚子里常常咕噜咕噜地响,反觉得很好玩。到了冬天,有一次吹着大北风,气候非常冷,我穿的一件棉袄,又薄又破了好几个大洞;走到青龙嘴上,实在受不了,便瞧着父亲在前面走远了,自己偷偷地溜了回来。但不肯把怕冷的情形说出口,只是倒在母亲怀里一言不发地赖着不去。母亲发现我这是第一次逃学,便哄着说:“儿好好读书,书读好后会发达起来要做官的。”我莫名其妙地最恨“要做官”的话,所以越发不肯去。母亲又说:“你父亲到学校后没有看到你,回来会打你一顿。”这才急了,要母亲送我一段路,终于去了。可是这次并没有挨打。父亲因为考了二三十年没有考到秀才,所以便有点做官迷,常常用做官来鼓励我;鼓励一次,便引起我一次心里极大的反感。母亲发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后,便再也不提这类的话。有时觉得父亲逼得我太紧了,所以她更不过问我读书的事情。过年过节,还帮我弄点小手脚,让我能多松一口气。 12岁我到县城住“高等小学”,每回家一次,走到塘角时,口里便叫着母亲,一直叫到家里,倒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;这种哭,是什么也不为的。15岁到武昌住省立第一师范,寒暑假回家,虽然不再哭,但一定要倒在母亲怀里嗲上半天的。大概直到民国十五年以后,才把这种情形给革命的气氛革掉了,而我已有二十多岁。我的幼儿帅军,常常和他的妈妈嗲得不像样子,使他的两个姐姐很生气;但我不太去理会,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时代。 以后我在外面的时候多,很难得有机会回到家里;即使回去一趟,也只住三五天便走了。一回到家,母亲便拉住我的手,要我陪着她坐。叔婶们向母亲开玩笑说,“你平时念秉常念得这厉害,现在回来了,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吧。”但母亲只是望着我默默地坐着,没有多少话和我说;而且在微笑中,神色总有点黯然。 六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,我由北平飞汉口,回到家里住了三四天。母亲一生的折磨,到了此时,生命的火光已所余无几;虽然没有病,已衰老得有时神智不清。我默默地挨着她一块儿坐着,母亲干枯的手拉着我的手,眼睛时时呆望着我的脸。这个罪孽深重的儿子,再也不会像从前样倒在她怀里,嗲着要她摸我的头,亲我的脸了。并且连在一块儿的默坐,也经常被亲友唤走。我本想隐居农村,过着多年梦想的种树养鱼的生活。但一回到农村,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,都是千疮百孔。而我双手空空,对他们,对自己,为安排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丝毫有所作为。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上的压力,只好又压着我奔向南京,以官为业。此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武昌住院了。我回到南京不久,哥哥死在武昌了,以大三分的利息借钱托友人代买棺材归葬故里,这对奄奄一息的母亲,当然是个大打击。此后,我带着妻子流亡。 (1970年3月《明报月刊》)
第一篇:捡树叶的母亲 深秋的夜晚格外宁静,晚饭后,我和母亲一起出门散步。 秋风骤起,枯叶簌簌而落。路上铺满了黄色的叶子,走上去感觉脚底软软的,很舒服。母亲看到满地的枯叶,脸上露出笑容,居然兴奋地对我说 :“看到这些树叶,真想捡啊!”我奇怪地问:“为什么呢?捡树叶干什么?”母亲说:“前几日我做了一个梦,梦到去树林里捡树叶,看到满地的树叶,好高兴啊!” 看见我询问的神情,母亲陷入了回忆,给我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。 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,有兄弟姐妹五个,母亲排行老三。每天天还没亮时,母亲就起床去村边的树林里捡树叶树枝,这是去收集全家这一整天用来生火做饭的柴火。最难熬的是冬天,雨雪天气多,但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、出门干活的外祖父能在临行前喝上一口热汤,仍然风雨无阻地去捡树叶。每当在冰天雪地发现一丛干草或干树叶时,母亲就像发现宝贝一样欢天喜地。 母亲经常说,自己就是个受累的命,结婚前每日在田间劳作,结婚后为了盖房子养孩子,更是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辛劳度日。甚至在我出生前的十几个小时,母亲还拖着臃肿的身子,在田地里辛苦地采棉花。 如今家庭条件改善许多,母亲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,这都是往日的苦日子让她养成的习惯,她知道生活的不易,所以从不奢侈浪费。 我随手捡起一片枯叶,遥想着旧时的那个少女捡起它时的快乐模样,心中有酸楚,也有温暖。 母亲曾温暖着一家人的生活,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,轮到我温暖您了,请您紧握我的手,让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日子。第二篇: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,只养活了我一个。那一年,农村闹瘟疫,一个月里,她死了三个孩子。爷爷对母亲说:“心里想不开,人就会疯。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!”后来,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,并常对家里人说:“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,你们不要管我。” 麦秋两季,母亲疯了似的劳动,每天鸡叫就到地里去,收割、打场,很晚才回到家里。她的身上都是土,头发上都是柴草,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。她的口号是:“争秋夺麦!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!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。”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。母亲把馍馍晾干了,再碾碎煮成糊喂我。我多病,每逢生病,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,祷告过往的神灵。母亲对人说:“我这个孩子,是不会孝顺的,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。” 家境小康以后,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之人,尽力周济。有两个远村的尼姑,每年麦秋收成后,总到我们家化缘。母亲除了给她们很多粮食,还常留她们食宿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,长得眉清目秀,冬天住在我家,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,夜里叫得很好听,我很想要。第二天清早,母亲告诉她,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。 一年春天,我从远方回来。母亲高兴得不知给我什么好。家里有一棵月季,父亲养了一春天,刚开了一朵大花,她折下就送给我了。父亲很心痛,母亲笑着说:“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,今天忽然开了呢,因为我的儿子回来,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!” 一九五六年,我在天津得了大病,要到外地去疗养。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,当我走出屋来,她站在廊子里,对我说:“别人病了往家里走,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!”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。我在外养病期间,母亲去世了,享年八十四岁。 蒋妍摘自《孙犁散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第三篇:我的母亲 位于台中市大度山坡上的东海大学的右界,与一批穷老百姓隔着一条乾溪。从乾溪的对岸,经常进入到东海校园的,除了一群穷孩子以外,还有一位老婆婆,身材瘦小,皱纹满面,头上披着半麻半白的头发。清早进来,捡被人抛弃掉的破烂。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。第一次偶然相遇,使我蓦然一惊,不觉用眼向她注视;她却很自然地把一只手抬一抬,向我打招呼,我心里更感到一阵难过。以后每遇到一次,心里就难过一次。有一天忍不住向我的妻说:“三四十年来,我每遇见一个穷苦的婆婆时,便想到自己的母亲。却没有像现在所经常遇见的这位捡破烂的婆婆,她的神情仿佛有点和母亲相像,虽然母亲不曾捡过破烂。你清好一包不穿的衣服,找着机会送给她,借以减少我遇见她时所引起的内心痛苦。” 现在我一个人客居香港,旧历年的除夕,离着我的生日只有三天。不在这一比较寂静的时间,把我对自己母亲的记忆记一点出来,恐怕散在天南地北的自己的儿女,再不容易有机会了解自己生命所自来的根生土长的家庭,是怎么一回事。但现在所能记忆的,已经模糊到不及百分之一二了。 一 浠水县的徐姓,大概是在元末明初从江西搬来的。统计有清一代,全县共有二百八十多名举人,我们这一姓,便占了八十几个。我们这一支,又分为军、民两分(读入声),这大概是由明代的屯卫制而来。在界河的徐姓是民分,而我们则是军分。 军分的祖先便是“琂”祖。村子的老人们都传说,他是赤手成家,变成了大地主的人。因为太有钱,所以房子起得非常讲究,房子左右两边,还做有“八”字形的两个斜面照墙,这是当时老百姓不应当有的,因此曾吃过一场官司。 琂祖死后,便葬在后面山上。在风水家的口中,说山形像凤,所以我们的村子便称为凤形塆。琂祖有六个儿子,乡下称为“六房”,我们是属于第六房的。 大概在曾祖父的时候,由地主而没落下来,生活开始困难。祖父弟兄三人,伯祖读书是贡生,我的祖父和叔祖种田。祖父生子二人,我的父亲居长,读书,叔父种田。伯祖生三子,大伯读书,二伯和六叔种田。叔祖生二子,都种田。若以共产党所定的标准说,我们都应算是中农。但在一连四个村子,共约七八十户人家中,他们几乎都赶不上我们;因为他们有的是佃户,种出一百斤稻子,地主要收去六十斤到七十斤,大抵新地主较老地主更为残刻;有的连佃田也没有。在我记忆中,横直二三十里地方的人民,除了几家大小地主外,富农、中农占十分之一二,其余都是一年不能吃饱几个月的穷苦农民。 二 我母亲姓杨,娘家在离我家约十华里的杨家塆,塆子比我们大;但除一两家外,都是穷困的佃户。据母亲告诉我,外婆是“远乡人”,洪、杨破南京时,躲在水沟里,士兵用矛向沟里搜索,颈碰着矛子穿了一个洞,幸而不死,辗转逃难到杨家塆,和外公结了婚,生有四子二女;我母亲在兄弟姊妹行,通计是第二,在姊妹行单计是老大。我稍能记事的时候,早已没有外婆外公。四个舅父中,除三舅父出继,可称富农外,大舅二舅都是忠厚穷苦的佃农。小舅出外佣工,有很长一段时间,在下巴河闻姓大地主(闻一多弟兄们家里)家中当厨子。当时大地主家里所给工人的工钱,比社会上一般的工钱还要低,因为工人吃的伙食比较好些。 母亲生于同治八年,大我父亲两岁。婚后生三男二女:大姐缉熙,后来嫁给“姚儿坳”的姚家。大哥纪常,种田,以胃癌死于民国三十五年。细姐在十五六岁时夭折,弟弟孚观读书无成,改在家里种田。 三 父亲读书非常用功,20岁左右,因肺病而吐血,吐得很厉害;幸亏祖母的调护,得以不死。父亲一直在乡下教蒙馆,收入非常微薄。家中三十石田(我们乡间,能收稻子一百斤的,便称为一石),全靠叔父耕种,勉强维持最低生活。所以母亲结婚后,除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外,弄饭、养猪等不待说,还要以“纺线子”为副业,工作非常辛苦。她的性情耿直而忠厚。我生下后,样子长得很难看,鼻孔向上,即使不会看相的人,也知道这是一种穷相;据说,父亲开始不大喜欢我。加以自小爱哭爱赌气,很少过一般小孩子欢天喜地的日子。 到了十几岁时,二妈曾和我聊天:“你现在读书很乖,但小时太吵人了。你妈妈整天忙进忙出的,你总是一面哭,一面吊住妈妈上褂的衣角儿,也随着吊出吊进,把你妈妈的上褂角儿都吊坏了。我们在侧面看不过眼,和她说,这样的孩子也舍不得打一顿?但你妈总是站住摸摸你的头,依然不肯打。”真的,在我的记忆里,只挨过父亲的狠打,却从来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。 后来,叔父和父亲分了家。叔父分十五石田和一点可以种棉花的旱地,自种自吃,加上过继的弟弟,生活当然比未分时过得好。但我们这一家六口,姐姐十三四岁,哥哥十一二岁,细姐十岁左右,我五六岁。父亲“高了脚”,不能下田;妈妈和姐姐的脚,包得像圆锥子样,更不能下田;哥哥开始学“庄稼”,但只能当助手;我只能上山去砍点柴,有时放放牛,但牛是与他人合伙养的。所以这样一点田,每年非要请半工或月工,便耕种不出。年成好,一年收一千五百斤稻子,做成七百五十斤米,每年只能吃到十二月过年的时候;一过了年,便凭父亲教蒙馆的一点“学钱”,四处托人情买米。 学钱除了应付家里各种差使和零用外,只够买两个多月的粮食,所以要接上四月大麦成熟,总还差一个多月。大麦成熟后,抢着雇人插秧,不能不把大麦糊给雇来的人吃。大麦吃完后,接着吃小麦;小麦吃完后要接上早稻成熟,中间也要缺一个月左右的粮;这便靠母亲和大姐起五更睡半夜的“纺线子”,哥哥拿到离家八里的黄泥嘴小镇市去卖。在一个完全停滞而没落的社会中,农民想用劳力换回一点养命钱,那种艰难的情形,不是现在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。大姐能干,好强,不愿家中露出穷相,工作得更是拼命。 四 村落四围是山,柴火应当不成问题。但不是因我家没有山,所以缺柴火,而是因为一连几个村子,都是穷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数,种树固然想不到,连自然生长的杂木,也不断被穷孩子偷得干干净净。大家不要的,只有长成一堆一堆的“狗儿刺”及其他带刺的藤状小灌木。家里不仅经常断米,也经常断柴。母亲没有办法,便常常临时拿着刀子找这类的东西,砍回来应急;砍一次,手上就带一次血。烧起来因为刚砍下是湿的,所以半天烧不着,湿烟熏得母亲的眼泪直流。一直到后来买了两块山,我和父亲在山上种下些松树苗,才慢慢解决了烧的问题。分得的一点地,是用来种棉花和长豆角的。夏天开始摘长豆角,接上秋天捡棉花,都由母亲包办。有时我也想跟着去,母亲说“你做不了什么,反而讨厌”,不准我去。现在回想起来,在夏、秋的烈日下,闷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间,母亲是怕我受不了。我们常常望到母亲肩上背着一满篮的豆角和棉花,弯着背,用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,笃笃地走回来;走到大门口,把肩上的篮子向门蹬上一放,坐在大门口的一块踏脚石上,上褂汗得透湿,脸上一粒一粒的汗珠还继续流。当我们围上去时还笑嘻嘻地摸着我们的头,捡几条好的豆角给我们生吃。在我的记忆中,只有当我发脾气,大吵大闹,因而挨父亲一顿狠打时,母亲才向父亲生过气,却不曾因为这种生活而出过怨言,生过气。她生性乐观,似乎也从不曾为这种生活而发过愁。 五 辛亥革命那一年,我开始从父亲发蒙读书,父亲这年设馆在离家三里的白洋河东岳庙里。在发蒙以前,父亲看到我做事比同年的小孩子认真,例如一群孩子上山砍柴(实际是冬天砍枯了的茅草),大家总是先玩够了,再动手。我却心里挂着母亲,一股正经地砍;多了拿不动,便送给其他的孩子。放牛绝不让牛吃他人的一口禾稼,总要为牛找出一些好草来。又发现我有读书的天资,旁的孩子读《三字经》,背不上,我不知什么时候听了,一个字也不认识地代旁的孩子背。所以渐渐疼我起来。 这年三月,不知为什么,怎样也买不到米,结果买了两斗豌豆,一直煎豌豆汤当饭吃,走到路上,肚子里常常咕噜咕噜地响,反觉得很好玩。到了冬天,有一次吹着大北风,气候非常冷,我穿的一件棉袄,又薄又破了好几个大洞;走到青龙嘴上,实在受不了,便瞧着父亲在前面走远了,自己偷偷地溜了回来。但不肯把怕冷的情形说出口,只是倒在母亲怀里一言不发地赖着不去。母亲发现我这是第一次逃学,便哄着说:“儿好好读书,书读好后会发达起来要做官的。”我莫名其妙地最恨“要做官”的话,所以越发不肯去。母亲又说:“你父亲到学校后没有看到你,回来会打你一顿。”这才急了,要母亲送我一段路,终于去了。可是这次并没有挨打。父亲因为考了二三十年没有考到秀才,所以便有点做官迷,常常用做官来鼓励我;鼓励一次,便引起我一次心里极大的反感。母亲发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后,便再也不提这类的话。有时觉得父亲逼得我太紧了,所以她更不过问我读书的事情。过年过节,还帮我弄点小手脚,让我能多松一口气。 12岁我到县城住“高等小学”,每回家一次,走到塘角时,口里便叫着母亲,一直叫到家里,倒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;这种哭,是什么也不为的。15岁到武昌住省立第一师范,寒暑假回家,虽然不再哭,但一定要倒在母亲怀里嗲上半天的。大概直到民国十五年以后,才把这种情形给革命的气氛革掉了,而我已有二十多岁。我的幼儿帅军,常常和他的妈妈嗲得不像样子,使他的两个姐姐很生气;但我不太去理会,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时代。 以后我在外面的时候多,很难得有机会回到家里;即使回去一趟,也只住三五天便走了。一回到家,母亲便拉住我的手,要我陪着她坐。叔婶们向母亲开玩笑说,“你平时念秉常念得这厉害,现在回来了,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吧。”但母亲只是望着我默默地坐着,没有多少话和我说;而且在微笑中,神色总有点黯然。 六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,我由北平飞汉口,回到家里住了三四天。母亲一生的折磨,到了此时,生命的火光已所余无几;虽然没有病,已衰老得有时神智不清。我默默地挨着她一块儿坐着,母亲干枯的手拉着我的手,眼睛时时呆望着我的脸。这个罪孽深重的儿子,再也不会像从前样倒在她怀里,嗲着要她摸我的头,亲我的脸了。并且连在一块儿的默坐,也经常被亲友唤走。我本想隐居农村,过着多年梦想的种树养鱼的生活。但一回到农村,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,都是千疮百孔。而我双手空空,对他们,对自己,为安排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丝毫有所作为。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上的压力,只好又压着我奔向南京,以官为业。此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武昌住院了。我回到南京不久,哥哥死在武昌了,以大三分的利息借钱托友人代买棺材归葬故里,这对奄奄一息的母亲,当然是个大打击。此后,我带着妻子流亡。 (1970年3月《明报月刊》)
我和我的母亲
2022-05-08 14:04:40
无锡英才网
那些年,我们的童年一直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,那些年,我们有一个时刻爱护着我们的母亲,那些年,总有一丝牵挂留在我们的心中,伴随着我们成长,答案网编辑特收集三篇与母亲有关的美文,希望网友们喜欢。 第一篇:捡树叶的母亲 深秋的夜晚格外宁静,晚饭后,我和母亲一起出门散步。 秋风骤起,枯叶簌簌而落。路上铺满了黄色的叶子,走上去感觉脚底软软的,很舒服。母亲看到满地的枯叶,脸上露出笑容,居然兴奋地对我说 :“看到这些树叶,真想捡啊!”我奇怪地问:“为什么呢?捡树叶干什么?”母亲说:“前几日我做了一个梦,梦到去树林里捡树叶,看到满地的树叶,好高兴啊!” 看见我询问的神情,母亲陷入了回忆,给我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。 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,有兄弟姐妹五个,母亲排行老三。每天天还没亮时,母亲就起床去村边的树林里捡树叶树枝,这是去收集全家这一整天用来生火做饭的柴火。最难熬的是冬天,雨雪天气多,但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、出门干活的外祖父能在临行前喝上一口热汤,仍然风雨无阻地去捡树叶。每当在冰天雪地发现一丛干草或干树叶时,母亲就像发现宝贝一样欢天喜地。 母亲经常说,自己就是个受累的命,结婚前每日在田间劳作,结婚后为了盖房子养孩子,更是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辛劳度日。甚至在我出生前的十几个小时,母亲还拖着臃肿的身子,在田地里辛苦地采棉花。 如今家庭条件改善许多,母亲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,这都是往日的苦日子让她养成的习惯,她知道生活的不易,所以从不奢侈浪费。 我随手捡起一片枯叶,遥想着旧时的那个少女捡起它时的快乐模样,心中有酸楚,也有温暖。 母亲曾温暖着一家人的生活,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,轮到我温暖您了,请您紧握我的手,让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日子。第二篇: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,只养活了我一个。那一年,农村闹瘟疫,一个月里,她死了三个孩子。爷爷对母亲说:“心里想不开,人就会疯。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!”后来,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,并常对家里人说:“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,你们不要管我。” 麦秋两季,母亲疯了似的劳动,每天鸡叫就到地里去,收割、打场,很晚才回到家里。她的身上都是土,头发上都是柴草,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。她的口号是:“争秋夺麦!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!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。”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。母亲把馍馍晾干了,再碾碎煮成糊喂我。我多病,每逢生病,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,祷告过往的神灵。母亲对人说:“我这个孩子,是不会孝顺的,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。” 家境小康以后,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之人,尽力周济。有两个远村的尼姑,每年麦秋收成后,总到我们家化缘。母亲除了给她们很多粮食,还常留她们食宿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,长得眉清目秀,冬天住在我家,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,夜里叫得很好听,我很想要。第二天清早,母亲告诉她,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。 一年春天,我从远方回来。母亲高兴得不知给我什么好。家里有一棵月季,父亲养了一春天,刚开了一朵大花,她折下就送给我了。父亲很心痛,母亲笑着说:“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,今天忽然开了呢,因为我的儿子回来,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!” 一九五六年,我在天津得了大病,要到外地去疗养。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,当我走出屋来,她站在廊子里,对我说:“别人病了往家里走,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!”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。我在外养病期间,母亲去世了,享年八十四岁。 蒋妍摘自《孙犁散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第三篇:我的母亲 位于台中市大度山坡上的东海大学的右界,与一批穷老百姓隔着一条乾溪。从乾溪的对岸,经常进入到东海校园的,除了一群穷孩子以外,还有一位老婆婆,身材瘦小,皱纹满面,头上披着半麻半白的头发。清早进来,捡被人抛弃掉的破烂。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。第一次偶然相遇,使我蓦然一惊,不觉用眼向她注视;她却很自然地把一只手抬一抬,向我打招呼,我心里更感到一阵难过。以后每遇到一次,心里就难过一次。有一天忍不住向我的妻说:“三四十年来,我每遇见一个穷苦的婆婆时,便想到自己的母亲。却没有像现在所经常遇见的这位捡破烂的婆婆,她的神情仿佛有点和母亲相像,虽然母亲不曾捡过破烂。你清好一包不穿的衣服,找着机会送给她,借以减少我遇见她时所引起的内心痛苦。” 现在我一个人客居香港,旧历年的除夕,离着我的生日只有三天。不在这一比较寂静的时间,把我对自己母亲的记忆记一点出来,恐怕散在天南地北的自己的儿女,再不容易有机会了解自己生命所自来的根生土长的家庭,是怎么一回事。但现在所能记忆的,已经模糊到不及百分之一二了。 一 浠水县的徐姓,大概是在元末明初从江西搬来的。统计有清一代,全县共有二百八十多名举人,我们这一姓,便占了八十几个。我们这一支,又分为军、民两分(读入声),这大概是由明代的屯卫制而来。在界河的徐姓是民分,而我们则是军分。 军分的祖先便是“琂”祖。村子的老人们都传说,他是赤手成家,变成了大地主的人。因为太有钱,所以房子起得非常讲究,房子左右两边,还做有“八”字形的两个斜面照墙,这是当时老百姓不应当有的,因此曾吃过一场官司。 琂祖死后,便葬在后面山上。在风水家的口中,说山形像凤,所以我们的村子便称为凤形塆。琂祖有六个儿子,乡下称为“六房”,我们是属于第六房的。 大概在曾祖父的时候,由地主而没落下来,生活开始困难。祖父弟兄三人,伯祖读书是贡生,我的祖父和叔祖种田。祖父生子二人,我的父亲居长,读书,叔父种田。伯祖生三子,大伯读书,二伯和六叔种田。叔祖生二子,都种田。若以共产党所定的标准说,我们都应算是中农。但在一连四个村子,共约七八十户人家中,他们几乎都赶不上我们;因为他们有的是佃户,种出一百斤稻子,地主要收去六十斤到七十斤,大抵新地主较老地主更为残刻;有的连佃田也没有。在我记忆中,横直二三十里地方的人民,除了几家大小地主外,富农、中农占十分之一二,其余都是一年不能吃饱几个月的穷苦农民。 二 我母亲姓杨,娘家在离我家约十华里的杨家塆,塆子比我们大;但除一两家外,都是穷困的佃户。据母亲告诉我,外婆是“远乡人”,洪、杨破南京时,躲在水沟里,士兵用矛向沟里搜索,颈碰着矛子穿了一个洞,幸而不死,辗转逃难到杨家塆,和外公结了婚,生有四子二女;我母亲在兄弟姊妹行,通计是第二,在姊妹行单计是老大。我稍能记事的时候,早已没有外婆外公。四个舅父中,除三舅父出继,可称富农外,大舅二舅都是忠厚穷苦的佃农。小舅出外佣工,有很长一段时间,在下巴河闻姓大地主(闻一多弟兄们家里)家中当厨子。当时大地主家里所给工人的工钱,比社会上一般的工钱还要低,因为工人吃的伙食比较好些。 母亲生于同治八年,大我父亲两岁。婚后生三男二女:大姐缉熙,后来嫁给“姚儿坳”的姚家。大哥纪常,种田,以胃癌死于民国三十五年。细姐在十五六岁时夭折,弟弟孚观读书无成,改在家里种田。 三 父亲读书非常用功,20岁左右,因肺病而吐血,吐得很厉害;幸亏祖母的调护,得以不死。父亲一直在乡下教蒙馆,收入非常微薄。家中三十石田(我们乡间,能收稻子一百斤的,便称为一石),全靠叔父耕种,勉强维持最低生活。所以母亲结婚后,除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外,弄饭、养猪等不待说,还要以“纺线子”为副业,工作非常辛苦。她的性情耿直而忠厚。我生下后,样子长得很难看,鼻孔向上,即使不会看相的人,也知道这是一种穷相;据说,父亲开始不大喜欢我。加以自小爱哭爱赌气,很少过一般小孩子欢天喜地的日子。 到了十几岁时,二妈曾和我聊天:“你现在读书很乖,但小时太吵人了。你妈妈整天忙进忙出的,你总是一面哭,一面吊住妈妈上褂的衣角儿,也随着吊出吊进,把你妈妈的上褂角儿都吊坏了。我们在侧面看不过眼,和她说,这样的孩子也舍不得打一顿?但你妈总是站住摸摸你的头,依然不肯打。”真的,在我的记忆里,只挨过父亲的狠打,却从来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。 后来,叔父和父亲分了家。叔父分十五石田和一点可以种棉花的旱地,自种自吃,加上过继的弟弟,生活当然比未分时过得好。但我们这一家六口,姐姐十三四岁,哥哥十一二岁,细姐十岁左右,我五六岁。父亲“高了脚”,不能下田;妈妈和姐姐的脚,包得像圆锥子样,更不能下田;哥哥开始学“庄稼”,但只能当助手;我只能上山去砍点柴,有时放放牛,但牛是与他人合伙养的。所以这样一点田,每年非要请半工或月工,便耕种不出。年成好,一年收一千五百斤稻子,做成七百五十斤米,每年只能吃到十二月过年的时候;一过了年,便凭父亲教蒙馆的一点“学钱”,四处托人情买米。 学钱除了应付家里各种差使和零用外,只够买两个多月的粮食,所以要接上四月大麦成熟,总还差一个多月。大麦成熟后,抢着雇人插秧,不能不把大麦糊给雇来的人吃。大麦吃完后,接着吃小麦;小麦吃完后要接上早稻成熟,中间也要缺一个月左右的粮;这便靠母亲和大姐起五更睡半夜的“纺线子”,哥哥拿到离家八里的黄泥嘴小镇市去卖。在一个完全停滞而没落的社会中,农民想用劳力换回一点养命钱,那种艰难的情形,不是现在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。大姐能干,好强,不愿家中露出穷相,工作得更是拼命。 四 村落四围是山,柴火应当不成问题。但不是因我家没有山,所以缺柴火,而是因为一连几个村子,都是穷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数,种树固然想不到,连自然生长的杂木,也不断被穷孩子偷得干干净净。大家不要的,只有长成一堆一堆的“狗儿刺”及其他带刺的藤状小灌木。家里不仅经常断米,也经常断柴。母亲没有办法,便常常临时拿着刀子找这类的东西,砍回来应急;砍一次,手上就带一次血。烧起来因为刚砍下是湿的,所以半天烧不着,湿烟熏得母亲的眼泪直流。一直到后来买了两块山,我和父亲在山上种下些松树苗,才慢慢解决了烧的问题。分得的一点地,是用来种棉花和长豆角的。夏天开始摘长豆角,接上秋天捡棉花,都由母亲包办。有时我也想跟着去,母亲说“你做不了什么,反而讨厌”,不准我去。现在回想起来,在夏、秋的烈日下,闷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间,母亲是怕我受不了。我们常常望到母亲肩上背着一满篮的豆角和棉花,弯着背,用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,笃笃地走回来;走到大门口,把肩上的篮子向门蹬上一放,坐在大门口的一块踏脚石上,上褂汗得透湿,脸上一粒一粒的汗珠还继续流。当我们围上去时还笑嘻嘻地摸着我们的头,捡几条好的豆角给我们生吃。在我的记忆中,只有当我发脾气,大吵大闹,因而挨父亲一顿狠打时,母亲才向父亲生过气,却不曾因为这种生活而出过怨言,生过气。她生性乐观,似乎也从不曾为这种生活而发过愁。 五 辛亥革命那一年,我开始从父亲发蒙读书,父亲这年设馆在离家三里的白洋河东岳庙里。在发蒙以前,父亲看到我做事比同年的小孩子认真,例如一群孩子上山砍柴(实际是冬天砍枯了的茅草),大家总是先玩够了,再动手。我却心里挂着母亲,一股正经地砍;多了拿不动,便送给其他的孩子。放牛绝不让牛吃他人的一口禾稼,总要为牛找出一些好草来。又发现我有读书的天资,旁的孩子读《三字经》,背不上,我不知什么时候听了,一个字也不认识地代旁的孩子背。所以渐渐疼我起来。 这年三月,不知为什么,怎样也买不到米,结果买了两斗豌豆,一直煎豌豆汤当饭吃,走到路上,肚子里常常咕噜咕噜地响,反觉得很好玩。到了冬天,有一次吹着大北风,气候非常冷,我穿的一件棉袄,又薄又破了好几个大洞;走到青龙嘴上,实在受不了,便瞧着父亲在前面走远了,自己偷偷地溜了回来。但不肯把怕冷的情形说出口,只是倒在母亲怀里一言不发地赖着不去。母亲发现我这是第一次逃学,便哄着说:“儿好好读书,书读好后会发达起来要做官的。”我莫名其妙地最恨“要做官”的话,所以越发不肯去。母亲又说:“你父亲到学校后没有看到你,回来会打你一顿。”这才急了,要母亲送我一段路,终于去了。可是这次并没有挨打。父亲因为考了二三十年没有考到秀才,所以便有点做官迷,常常用做官来鼓励我;鼓励一次,便引起我一次心里极大的反感。母亲发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后,便再也不提这类的话。有时觉得父亲逼得我太紧了,所以她更不过问我读书的事情。过年过节,还帮我弄点小手脚,让我能多松一口气。 12岁我到县城住“高等小学”,每回家一次,走到塘角时,口里便叫着母亲,一直叫到家里,倒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;这种哭,是什么也不为的。15岁到武昌住省立第一师范,寒暑假回家,虽然不再哭,但一定要倒在母亲怀里嗲上半天的。大概直到民国十五年以后,才把这种情形给革命的气氛革掉了,而我已有二十多岁。我的幼儿帅军,常常和他的妈妈嗲得不像样子,使他的两个姐姐很生气;但我不太去理会,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时代。 以后我在外面的时候多,很难得有机会回到家里;即使回去一趟,也只住三五天便走了。一回到家,母亲便拉住我的手,要我陪着她坐。叔婶们向母亲开玩笑说,“你平时念秉常念得这厉害,现在回来了,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吧。”但母亲只是望着我默默地坐着,没有多少话和我说;而且在微笑中,神色总有点黯然。 六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,我由北平飞汉口,回到家里住了三四天。母亲一生的折磨,到了此时,生命的火光已所余无几;虽然没有病,已衰老得有时神智不清。我默默地挨着她一块儿坐着,母亲干枯的手拉着我的手,眼睛时时呆望着我的脸。这个罪孽深重的儿子,再也不会像从前样倒在她怀里,嗲着要她摸我的头,亲我的脸了。并且连在一块儿的默坐,也经常被亲友唤走。我本想隐居农村,过着多年梦想的种树养鱼的生活。但一回到农村,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,都是千疮百孔。而我双手空空,对他们,对自己,为安排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丝毫有所作为。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上的压力,只好又压着我奔向南京,以官为业。此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武昌住院了。我回到南京不久,哥哥死在武昌了,以大三分的利息借钱托友人代买棺材归葬故里,这对奄奄一息的母亲,当然是个大打击。此后,我带着妻子流亡。 (1970年3月《明报月刊》)
第一篇:捡树叶的母亲 深秋的夜晚格外宁静,晚饭后,我和母亲一起出门散步。 秋风骤起,枯叶簌簌而落。路上铺满了黄色的叶子,走上去感觉脚底软软的,很舒服。母亲看到满地的枯叶,脸上露出笑容,居然兴奋地对我说 :“看到这些树叶,真想捡啊!”我奇怪地问:“为什么呢?捡树叶干什么?”母亲说:“前几日我做了一个梦,梦到去树林里捡树叶,看到满地的树叶,好高兴啊!” 看见我询问的神情,母亲陷入了回忆,给我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。 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,有兄弟姐妹五个,母亲排行老三。每天天还没亮时,母亲就起床去村边的树林里捡树叶树枝,这是去收集全家这一整天用来生火做饭的柴火。最难熬的是冬天,雨雪天气多,但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、出门干活的外祖父能在临行前喝上一口热汤,仍然风雨无阻地去捡树叶。每当在冰天雪地发现一丛干草或干树叶时,母亲就像发现宝贝一样欢天喜地。 母亲经常说,自己就是个受累的命,结婚前每日在田间劳作,结婚后为了盖房子养孩子,更是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辛劳度日。甚至在我出生前的十几个小时,母亲还拖着臃肿的身子,在田地里辛苦地采棉花。 如今家庭条件改善许多,母亲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,这都是往日的苦日子让她养成的习惯,她知道生活的不易,所以从不奢侈浪费。 我随手捡起一片枯叶,遥想着旧时的那个少女捡起它时的快乐模样,心中有酸楚,也有温暖。 母亲曾温暖着一家人的生活,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,轮到我温暖您了,请您紧握我的手,让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日子。第二篇: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,只养活了我一个。那一年,农村闹瘟疫,一个月里,她死了三个孩子。爷爷对母亲说:“心里想不开,人就会疯。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!”后来,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,并常对家里人说:“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,你们不要管我。” 麦秋两季,母亲疯了似的劳动,每天鸡叫就到地里去,收割、打场,很晚才回到家里。她的身上都是土,头发上都是柴草,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。她的口号是:“争秋夺麦!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!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。”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。母亲把馍馍晾干了,再碾碎煮成糊喂我。我多病,每逢生病,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,祷告过往的神灵。母亲对人说:“我这个孩子,是不会孝顺的,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。” 家境小康以后,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之人,尽力周济。有两个远村的尼姑,每年麦秋收成后,总到我们家化缘。母亲除了给她们很多粮食,还常留她们食宿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,长得眉清目秀,冬天住在我家,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,夜里叫得很好听,我很想要。第二天清早,母亲告诉她,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。 一年春天,我从远方回来。母亲高兴得不知给我什么好。家里有一棵月季,父亲养了一春天,刚开了一朵大花,她折下就送给我了。父亲很心痛,母亲笑着说:“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,今天忽然开了呢,因为我的儿子回来,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!” 一九五六年,我在天津得了大病,要到外地去疗养。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,当我走出屋来,她站在廊子里,对我说:“别人病了往家里走,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!”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。我在外养病期间,母亲去世了,享年八十四岁。 蒋妍摘自《孙犁散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第三篇:我的母亲 位于台中市大度山坡上的东海大学的右界,与一批穷老百姓隔着一条乾溪。从乾溪的对岸,经常进入到东海校园的,除了一群穷孩子以外,还有一位老婆婆,身材瘦小,皱纹满面,头上披着半麻半白的头发。清早进来,捡被人抛弃掉的破烂。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。第一次偶然相遇,使我蓦然一惊,不觉用眼向她注视;她却很自然地把一只手抬一抬,向我打招呼,我心里更感到一阵难过。以后每遇到一次,心里就难过一次。有一天忍不住向我的妻说:“三四十年来,我每遇见一个穷苦的婆婆时,便想到自己的母亲。却没有像现在所经常遇见的这位捡破烂的婆婆,她的神情仿佛有点和母亲相像,虽然母亲不曾捡过破烂。你清好一包不穿的衣服,找着机会送给她,借以减少我遇见她时所引起的内心痛苦。” 现在我一个人客居香港,旧历年的除夕,离着我的生日只有三天。不在这一比较寂静的时间,把我对自己母亲的记忆记一点出来,恐怕散在天南地北的自己的儿女,再不容易有机会了解自己生命所自来的根生土长的家庭,是怎么一回事。但现在所能记忆的,已经模糊到不及百分之一二了。 一 浠水县的徐姓,大概是在元末明初从江西搬来的。统计有清一代,全县共有二百八十多名举人,我们这一姓,便占了八十几个。我们这一支,又分为军、民两分(读入声),这大概是由明代的屯卫制而来。在界河的徐姓是民分,而我们则是军分。 军分的祖先便是“琂”祖。村子的老人们都传说,他是赤手成家,变成了大地主的人。因为太有钱,所以房子起得非常讲究,房子左右两边,还做有“八”字形的两个斜面照墙,这是当时老百姓不应当有的,因此曾吃过一场官司。 琂祖死后,便葬在后面山上。在风水家的口中,说山形像凤,所以我们的村子便称为凤形塆。琂祖有六个儿子,乡下称为“六房”,我们是属于第六房的。 大概在曾祖父的时候,由地主而没落下来,生活开始困难。祖父弟兄三人,伯祖读书是贡生,我的祖父和叔祖种田。祖父生子二人,我的父亲居长,读书,叔父种田。伯祖生三子,大伯读书,二伯和六叔种田。叔祖生二子,都种田。若以共产党所定的标准说,我们都应算是中农。但在一连四个村子,共约七八十户人家中,他们几乎都赶不上我们;因为他们有的是佃户,种出一百斤稻子,地主要收去六十斤到七十斤,大抵新地主较老地主更为残刻;有的连佃田也没有。在我记忆中,横直二三十里地方的人民,除了几家大小地主外,富农、中农占十分之一二,其余都是一年不能吃饱几个月的穷苦农民。 二 我母亲姓杨,娘家在离我家约十华里的杨家塆,塆子比我们大;但除一两家外,都是穷困的佃户。据母亲告诉我,外婆是“远乡人”,洪、杨破南京时,躲在水沟里,士兵用矛向沟里搜索,颈碰着矛子穿了一个洞,幸而不死,辗转逃难到杨家塆,和外公结了婚,生有四子二女;我母亲在兄弟姊妹行,通计是第二,在姊妹行单计是老大。我稍能记事的时候,早已没有外婆外公。四个舅父中,除三舅父出继,可称富农外,大舅二舅都是忠厚穷苦的佃农。小舅出外佣工,有很长一段时间,在下巴河闻姓大地主(闻一多弟兄们家里)家中当厨子。当时大地主家里所给工人的工钱,比社会上一般的工钱还要低,因为工人吃的伙食比较好些。 母亲生于同治八年,大我父亲两岁。婚后生三男二女:大姐缉熙,后来嫁给“姚儿坳”的姚家。大哥纪常,种田,以胃癌死于民国三十五年。细姐在十五六岁时夭折,弟弟孚观读书无成,改在家里种田。 三 父亲读书非常用功,20岁左右,因肺病而吐血,吐得很厉害;幸亏祖母的调护,得以不死。父亲一直在乡下教蒙馆,收入非常微薄。家中三十石田(我们乡间,能收稻子一百斤的,便称为一石),全靠叔父耕种,勉强维持最低生活。所以母亲结婚后,除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外,弄饭、养猪等不待说,还要以“纺线子”为副业,工作非常辛苦。她的性情耿直而忠厚。我生下后,样子长得很难看,鼻孔向上,即使不会看相的人,也知道这是一种穷相;据说,父亲开始不大喜欢我。加以自小爱哭爱赌气,很少过一般小孩子欢天喜地的日子。 到了十几岁时,二妈曾和我聊天:“你现在读书很乖,但小时太吵人了。你妈妈整天忙进忙出的,你总是一面哭,一面吊住妈妈上褂的衣角儿,也随着吊出吊进,把你妈妈的上褂角儿都吊坏了。我们在侧面看不过眼,和她说,这样的孩子也舍不得打一顿?但你妈总是站住摸摸你的头,依然不肯打。”真的,在我的记忆里,只挨过父亲的狠打,却从来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。 后来,叔父和父亲分了家。叔父分十五石田和一点可以种棉花的旱地,自种自吃,加上过继的弟弟,生活当然比未分时过得好。但我们这一家六口,姐姐十三四岁,哥哥十一二岁,细姐十岁左右,我五六岁。父亲“高了脚”,不能下田;妈妈和姐姐的脚,包得像圆锥子样,更不能下田;哥哥开始学“庄稼”,但只能当助手;我只能上山去砍点柴,有时放放牛,但牛是与他人合伙养的。所以这样一点田,每年非要请半工或月工,便耕种不出。年成好,一年收一千五百斤稻子,做成七百五十斤米,每年只能吃到十二月过年的时候;一过了年,便凭父亲教蒙馆的一点“学钱”,四处托人情买米。 学钱除了应付家里各种差使和零用外,只够买两个多月的粮食,所以要接上四月大麦成熟,总还差一个多月。大麦成熟后,抢着雇人插秧,不能不把大麦糊给雇来的人吃。大麦吃完后,接着吃小麦;小麦吃完后要接上早稻成熟,中间也要缺一个月左右的粮;这便靠母亲和大姐起五更睡半夜的“纺线子”,哥哥拿到离家八里的黄泥嘴小镇市去卖。在一个完全停滞而没落的社会中,农民想用劳力换回一点养命钱,那种艰难的情形,不是现在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。大姐能干,好强,不愿家中露出穷相,工作得更是拼命。 四 村落四围是山,柴火应当不成问题。但不是因我家没有山,所以缺柴火,而是因为一连几个村子,都是穷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数,种树固然想不到,连自然生长的杂木,也不断被穷孩子偷得干干净净。大家不要的,只有长成一堆一堆的“狗儿刺”及其他带刺的藤状小灌木。家里不仅经常断米,也经常断柴。母亲没有办法,便常常临时拿着刀子找这类的东西,砍回来应急;砍一次,手上就带一次血。烧起来因为刚砍下是湿的,所以半天烧不着,湿烟熏得母亲的眼泪直流。一直到后来买了两块山,我和父亲在山上种下些松树苗,才慢慢解决了烧的问题。分得的一点地,是用来种棉花和长豆角的。夏天开始摘长豆角,接上秋天捡棉花,都由母亲包办。有时我也想跟着去,母亲说“你做不了什么,反而讨厌”,不准我去。现在回想起来,在夏、秋的烈日下,闷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间,母亲是怕我受不了。我们常常望到母亲肩上背着一满篮的豆角和棉花,弯着背,用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,笃笃地走回来;走到大门口,把肩上的篮子向门蹬上一放,坐在大门口的一块踏脚石上,上褂汗得透湿,脸上一粒一粒的汗珠还继续流。当我们围上去时还笑嘻嘻地摸着我们的头,捡几条好的豆角给我们生吃。在我的记忆中,只有当我发脾气,大吵大闹,因而挨父亲一顿狠打时,母亲才向父亲生过气,却不曾因为这种生活而出过怨言,生过气。她生性乐观,似乎也从不曾为这种生活而发过愁。 五 辛亥革命那一年,我开始从父亲发蒙读书,父亲这年设馆在离家三里的白洋河东岳庙里。在发蒙以前,父亲看到我做事比同年的小孩子认真,例如一群孩子上山砍柴(实际是冬天砍枯了的茅草),大家总是先玩够了,再动手。我却心里挂着母亲,一股正经地砍;多了拿不动,便送给其他的孩子。放牛绝不让牛吃他人的一口禾稼,总要为牛找出一些好草来。又发现我有读书的天资,旁的孩子读《三字经》,背不上,我不知什么时候听了,一个字也不认识地代旁的孩子背。所以渐渐疼我起来。 这年三月,不知为什么,怎样也买不到米,结果买了两斗豌豆,一直煎豌豆汤当饭吃,走到路上,肚子里常常咕噜咕噜地响,反觉得很好玩。到了冬天,有一次吹着大北风,气候非常冷,我穿的一件棉袄,又薄又破了好几个大洞;走到青龙嘴上,实在受不了,便瞧着父亲在前面走远了,自己偷偷地溜了回来。但不肯把怕冷的情形说出口,只是倒在母亲怀里一言不发地赖着不去。母亲发现我这是第一次逃学,便哄着说:“儿好好读书,书读好后会发达起来要做官的。”我莫名其妙地最恨“要做官”的话,所以越发不肯去。母亲又说:“你父亲到学校后没有看到你,回来会打你一顿。”这才急了,要母亲送我一段路,终于去了。可是这次并没有挨打。父亲因为考了二三十年没有考到秀才,所以便有点做官迷,常常用做官来鼓励我;鼓励一次,便引起我一次心里极大的反感。母亲发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后,便再也不提这类的话。有时觉得父亲逼得我太紧了,所以她更不过问我读书的事情。过年过节,还帮我弄点小手脚,让我能多松一口气。 12岁我到县城住“高等小学”,每回家一次,走到塘角时,口里便叫着母亲,一直叫到家里,倒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;这种哭,是什么也不为的。15岁到武昌住省立第一师范,寒暑假回家,虽然不再哭,但一定要倒在母亲怀里嗲上半天的。大概直到民国十五年以后,才把这种情形给革命的气氛革掉了,而我已有二十多岁。我的幼儿帅军,常常和他的妈妈嗲得不像样子,使他的两个姐姐很生气;但我不太去理会,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时代。 以后我在外面的时候多,很难得有机会回到家里;即使回去一趟,也只住三五天便走了。一回到家,母亲便拉住我的手,要我陪着她坐。叔婶们向母亲开玩笑说,“你平时念秉常念得这厉害,现在回来了,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吧。”但母亲只是望着我默默地坐着,没有多少话和我说;而且在微笑中,神色总有点黯然。 六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,我由北平飞汉口,回到家里住了三四天。母亲一生的折磨,到了此时,生命的火光已所余无几;虽然没有病,已衰老得有时神智不清。我默默地挨着她一块儿坐着,母亲干枯的手拉着我的手,眼睛时时呆望着我的脸。这个罪孽深重的儿子,再也不会像从前样倒在她怀里,嗲着要她摸我的头,亲我的脸了。并且连在一块儿的默坐,也经常被亲友唤走。我本想隐居农村,过着多年梦想的种树养鱼的生活。但一回到农村,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,都是千疮百孔。而我双手空空,对他们,对自己,为安排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丝毫有所作为。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上的压力,只好又压着我奔向南京,以官为业。此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武昌住院了。我回到南京不久,哥哥死在武昌了,以大三分的利息借钱托友人代买棺材归葬故里,这对奄奄一息的母亲,当然是个大打击。此后,我带着妻子流亡。 (1970年3月《明报月刊》)
 第一篇:捡树叶的母亲 深秋的夜晚格外宁静,晚饭后,我和母亲一起出门散步。 秋风骤起,枯叶簌簌而落。路上铺满了黄色的叶子,走上去感觉脚底软软的,很舒服。母亲看到满地的枯叶,脸上露出笑容,居然兴奋地对我说 :“看到这些树叶,真想捡啊!”我奇怪地问:“为什么呢?捡树叶干什么?”母亲说:“前几日我做了一个梦,梦到去树林里捡树叶,看到满地的树叶,好高兴啊!” 看见我询问的神情,母亲陷入了回忆,给我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。 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,有兄弟姐妹五个,母亲排行老三。每天天还没亮时,母亲就起床去村边的树林里捡树叶树枝,这是去收集全家这一整天用来生火做饭的柴火。最难熬的是冬天,雨雪天气多,但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、出门干活的外祖父能在临行前喝上一口热汤,仍然风雨无阻地去捡树叶。每当在冰天雪地发现一丛干草或干树叶时,母亲就像发现宝贝一样欢天喜地。 母亲经常说,自己就是个受累的命,结婚前每日在田间劳作,结婚后为了盖房子养孩子,更是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辛劳度日。甚至在我出生前的十几个小时,母亲还拖着臃肿的身子,在田地里辛苦地采棉花。 如今家庭条件改善许多,母亲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,这都是往日的苦日子让她养成的习惯,她知道生活的不易,所以从不奢侈浪费。 我随手捡起一片枯叶,遥想着旧时的那个少女捡起它时的快乐模样,心中有酸楚,也有温暖。 母亲曾温暖着一家人的生活,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,轮到我温暖您了,请您紧握我的手,让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日子。第二篇: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,只养活了我一个。那一年,农村闹瘟疫,一个月里,她死了三个孩子。爷爷对母亲说:“心里想不开,人就会疯。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!”后来,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,并常对家里人说:“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,你们不要管我。” 麦秋两季,母亲疯了似的劳动,每天鸡叫就到地里去,收割、打场,很晚才回到家里。她的身上都是土,头发上都是柴草,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。她的口号是:“争秋夺麦!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!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。”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。母亲把馍馍晾干了,再碾碎煮成糊喂我。我多病,每逢生病,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,祷告过往的神灵。母亲对人说:“我这个孩子,是不会孝顺的,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。” 家境小康以后,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之人,尽力周济。有两个远村的尼姑,每年麦秋收成后,总到我们家化缘。母亲除了给她们很多粮食,还常留她们食宿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,长得眉清目秀,冬天住在我家,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,夜里叫得很好听,我很想要。第二天清早,母亲告诉她,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。 一年春天,我从远方回来。母亲高兴得不知给我什么好。家里有一棵月季,父亲养了一春天,刚开了一朵大花,她折下就送给我了。父亲很心痛,母亲笑着说:“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,今天忽然开了呢,因为我的儿子回来,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!” 一九五六年,我在天津得了大病,要到外地去疗养。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,当我走出屋来,她站在廊子里,对我说:“别人病了往家里走,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!”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。我在外养病期间,母亲去世了,享年八十四岁。 蒋妍摘自《孙犁散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第三篇:我的母亲 位于台中市大度山坡上的东海大学的右界,与一批穷老百姓隔着一条乾溪。从乾溪的对岸,经常进入到东海校园的,除了一群穷孩子以外,还有一位老婆婆,身材瘦小,皱纹满面,头上披着半麻半白的头发。清早进来,捡被人抛弃掉的破烂。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。第一次偶然相遇,使我蓦然一惊,不觉用眼向她注视;她却很自然地把一只手抬一抬,向我打招呼,我心里更感到一阵难过。以后每遇到一次,心里就难过一次。有一天忍不住向我的妻说:“三四十年来,我每遇见一个穷苦的婆婆时,便想到自己的母亲。却没有像现在所经常遇见的这位捡破烂的婆婆,她的神情仿佛有点和母亲相像,虽然母亲不曾捡过破烂。你清好一包不穿的衣服,找着机会送给她,借以减少我遇见她时所引起的内心痛苦。” 现在我一个人客居香港,旧历年的除夕,离着我的生日只有三天。不在这一比较寂静的时间,把我对自己母亲的记忆记一点出来,恐怕散在天南地北的自己的儿女,再不容易有机会了解自己生命所自来的根生土长的家庭,是怎么一回事。但现在所能记忆的,已经模糊到不及百分之一二了。 一 浠水县的徐姓,大概是在元末明初从江西搬来的。统计有清一代,全县共有二百八十多名举人,我们这一姓,便占了八十几个。我们这一支,又分为军、民两分(读入声),这大概是由明代的屯卫制而来。在界河的徐姓是民分,而我们则是军分。 军分的祖先便是“琂”祖。村子的老人们都传说,他是赤手成家,变成了大地主的人。因为太有钱,所以房子起得非常讲究,房子左右两边,还做有“八”字形的两个斜面照墙,这是当时老百姓不应当有的,因此曾吃过一场官司。 琂祖死后,便葬在后面山上。在风水家的口中,说山形像凤,所以我们的村子便称为凤形塆。琂祖有六个儿子,乡下称为“六房”,我们是属于第六房的。 大概在曾祖父的时候,由地主而没落下来,生活开始困难。祖父弟兄三人,伯祖读书是贡生,我的祖父和叔祖种田。祖父生子二人,我的父亲居长,读书,叔父种田。伯祖生三子,大伯读书,二伯和六叔种田。叔祖生二子,都种田。若以共产党所定的标准说,我们都应算是中农。但在一连四个村子,共约七八十户人家中,他们几乎都赶不上我们;因为他们有的是佃户,种出一百斤稻子,地主要收去六十斤到七十斤,大抵新地主较老地主更为残刻;有的连佃田也没有。在我记忆中,横直二三十里地方的人民,除了几家大小地主外,富农、中农占十分之一二,其余都是一年不能吃饱几个月的穷苦农民。 二 我母亲姓杨,娘家在离我家约十华里的杨家塆,塆子比我们大;但除一两家外,都是穷困的佃户。据母亲告诉我,外婆是“远乡人”,洪、杨破南京时,躲在水沟里,士兵用矛向沟里搜索,颈碰着矛子穿了一个洞,幸而不死,辗转逃难到杨家塆,和外公结了婚,生有四子二女;我母亲在兄弟姊妹行,通计是第二,在姊妹行单计是老大。我稍能记事的时候,早已没有外婆外公。四个舅父中,除三舅父出继,可称富农外,大舅二舅都是忠厚穷苦的佃农。小舅出外佣工,有很长一段时间,在下巴河闻姓大地主(闻一多弟兄们家里)家中当厨子。当时大地主家里所给工人的工钱,比社会上一般的工钱还要低,因为工人吃的伙食比较好些。 母亲生于同治八年,大我父亲两岁。婚后生三男二女:大姐缉熙,后来嫁给“姚儿坳”的姚家。大哥纪常,种田,以胃癌死于民国三十五年。细姐在十五六岁时夭折,弟弟孚观读书无成,改在家里种田。 三 父亲读书非常用功,20岁左右,因肺病而吐血,吐得很厉害;幸亏祖母的调护,得以不死。父亲一直在乡下教蒙馆,收入非常微薄。家中三十石田(我们乡间,能收稻子一百斤的,便称为一石),全靠叔父耕种,勉强维持最低生活。所以母亲结婚后,除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外,弄饭、养猪等不待说,还要以“纺线子”为副业,工作非常辛苦。她的性情耿直而忠厚。我生下后,样子长得很难看,鼻孔向上,即使不会看相的人,也知道这是一种穷相;据说,父亲开始不大喜欢我。加以自小爱哭爱赌气,很少过一般小孩子欢天喜地的日子。 到了十几岁时,二妈曾和我聊天:“你现在读书很乖,但小时太吵人了。你妈妈整天忙进忙出的,你总是一面哭,一面吊住妈妈上褂的衣角儿,也随着吊出吊进,把你妈妈的上褂角儿都吊坏了。我们在侧面看不过眼,和她说,这样的孩子也舍不得打一顿?但你妈总是站住摸摸你的头,依然不肯打。”真的,在我的记忆里,只挨过父亲的狠打,却从来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。 后来,叔父和父亲分了家。叔父分十五石田和一点可以种棉花的旱地,自种自吃,加上过继的弟弟,生活当然比未分时过得好。但我们这一家六口,姐姐十三四岁,哥哥十一二岁,细姐十岁左右,我五六岁。父亲“高了脚”,不能下田;妈妈和姐姐的脚,包得像圆锥子样,更不能下田;哥哥开始学“庄稼”,但只能当助手;我只能上山去砍点柴,有时放放牛,但牛是与他人合伙养的。所以这样一点田,每年非要请半工或月工,便耕种不出。年成好,一年收一千五百斤稻子,做成七百五十斤米,每年只能吃到十二月过年的时候;一过了年,便凭父亲教蒙馆的一点“学钱”,四处托人情买米。 学钱除了应付家里各种差使和零用外,只够买两个多月的粮食,所以要接上四月大麦成熟,总还差一个多月。大麦成熟后,抢着雇人插秧,不能不把大麦糊给雇来的人吃。大麦吃完后,接着吃小麦;小麦吃完后要接上早稻成熟,中间也要缺一个月左右的粮;这便靠母亲和大姐起五更睡半夜的“纺线子”,哥哥拿到离家八里的黄泥嘴小镇市去卖。在一个完全停滞而没落的社会中,农民想用劳力换回一点养命钱,那种艰难的情形,不是现在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。大姐能干,好强,不愿家中露出穷相,工作得更是拼命。 四 村落四围是山,柴火应当不成问题。但不是因我家没有山,所以缺柴火,而是因为一连几个村子,都是穷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数,种树固然想不到,连自然生长的杂木,也不断被穷孩子偷得干干净净。大家不要的,只有长成一堆一堆的“狗儿刺”及其他带刺的藤状小灌木。家里不仅经常断米,也经常断柴。母亲没有办法,便常常临时拿着刀子找这类的东西,砍回来应急;砍一次,手上就带一次血。烧起来因为刚砍下是湿的,所以半天烧不着,湿烟熏得母亲的眼泪直流。一直到后来买了两块山,我和父亲在山上种下些松树苗,才慢慢解决了烧的问题。分得的一点地,是用来种棉花和长豆角的。夏天开始摘长豆角,接上秋天捡棉花,都由母亲包办。有时我也想跟着去,母亲说“你做不了什么,反而讨厌”,不准我去。现在回想起来,在夏、秋的烈日下,闷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间,母亲是怕我受不了。我们常常望到母亲肩上背着一满篮的豆角和棉花,弯着背,用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,笃笃地走回来;走到大门口,把肩上的篮子向门蹬上一放,坐在大门口的一块踏脚石上,上褂汗得透湿,脸上一粒一粒的汗珠还继续流。当我们围上去时还笑嘻嘻地摸着我们的头,捡几条好的豆角给我们生吃。在我的记忆中,只有当我发脾气,大吵大闹,因而挨父亲一顿狠打时,母亲才向父亲生过气,却不曾因为这种生活而出过怨言,生过气。她生性乐观,似乎也从不曾为这种生活而发过愁。 五 辛亥革命那一年,我开始从父亲发蒙读书,父亲这年设馆在离家三里的白洋河东岳庙里。在发蒙以前,父亲看到我做事比同年的小孩子认真,例如一群孩子上山砍柴(实际是冬天砍枯了的茅草),大家总是先玩够了,再动手。我却心里挂着母亲,一股正经地砍;多了拿不动,便送给其他的孩子。放牛绝不让牛吃他人的一口禾稼,总要为牛找出一些好草来。又发现我有读书的天资,旁的孩子读《三字经》,背不上,我不知什么时候听了,一个字也不认识地代旁的孩子背。所以渐渐疼我起来。 这年三月,不知为什么,怎样也买不到米,结果买了两斗豌豆,一直煎豌豆汤当饭吃,走到路上,肚子里常常咕噜咕噜地响,反觉得很好玩。到了冬天,有一次吹着大北风,气候非常冷,我穿的一件棉袄,又薄又破了好几个大洞;走到青龙嘴上,实在受不了,便瞧着父亲在前面走远了,自己偷偷地溜了回来。但不肯把怕冷的情形说出口,只是倒在母亲怀里一言不发地赖着不去。母亲发现我这是第一次逃学,便哄着说:“儿好好读书,书读好后会发达起来要做官的。”我莫名其妙地最恨“要做官”的话,所以越发不肯去。母亲又说:“你父亲到学校后没有看到你,回来会打你一顿。”这才急了,要母亲送我一段路,终于去了。可是这次并没有挨打。父亲因为考了二三十年没有考到秀才,所以便有点做官迷,常常用做官来鼓励我;鼓励一次,便引起我一次心里极大的反感。母亲发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后,便再也不提这类的话。有时觉得父亲逼得我太紧了,所以她更不过问我读书的事情。过年过节,还帮我弄点小手脚,让我能多松一口气。 12岁我到县城住“高等小学”,每回家一次,走到塘角时,口里便叫着母亲,一直叫到家里,倒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;这种哭,是什么也不为的。15岁到武昌住省立第一师范,寒暑假回家,虽然不再哭,但一定要倒在母亲怀里嗲上半天的。大概直到民国十五年以后,才把这种情形给革命的气氛革掉了,而我已有二十多岁。我的幼儿帅军,常常和他的妈妈嗲得不像样子,使他的两个姐姐很生气;但我不太去理会,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时代。 以后我在外面的时候多,很难得有机会回到家里;即使回去一趟,也只住三五天便走了。一回到家,母亲便拉住我的手,要我陪着她坐。叔婶们向母亲开玩笑说,“你平时念秉常念得这厉害,现在回来了,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吧。”但母亲只是望着我默默地坐着,没有多少话和我说;而且在微笑中,神色总有点黯然。 六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,我由北平飞汉口,回到家里住了三四天。母亲一生的折磨,到了此时,生命的火光已所余无几;虽然没有病,已衰老得有时神智不清。我默默地挨着她一块儿坐着,母亲干枯的手拉着我的手,眼睛时时呆望着我的脸。这个罪孽深重的儿子,再也不会像从前样倒在她怀里,嗲着要她摸我的头,亲我的脸了。并且连在一块儿的默坐,也经常被亲友唤走。我本想隐居农村,过着多年梦想的种树养鱼的生活。但一回到农村,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,都是千疮百孔。而我双手空空,对他们,对自己,为安排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丝毫有所作为。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上的压力,只好又压着我奔向南京,以官为业。此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武昌住院了。我回到南京不久,哥哥死在武昌了,以大三分的利息借钱托友人代买棺材归葬故里,这对奄奄一息的母亲,当然是个大打击。此后,我带着妻子流亡。 (1970年3月《明报月刊》)
第一篇:捡树叶的母亲 深秋的夜晚格外宁静,晚饭后,我和母亲一起出门散步。 秋风骤起,枯叶簌簌而落。路上铺满了黄色的叶子,走上去感觉脚底软软的,很舒服。母亲看到满地的枯叶,脸上露出笑容,居然兴奋地对我说 :“看到这些树叶,真想捡啊!”我奇怪地问:“为什么呢?捡树叶干什么?”母亲说:“前几日我做了一个梦,梦到去树林里捡树叶,看到满地的树叶,好高兴啊!” 看见我询问的神情,母亲陷入了回忆,给我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。 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,有兄弟姐妹五个,母亲排行老三。每天天还没亮时,母亲就起床去村边的树林里捡树叶树枝,这是去收集全家这一整天用来生火做饭的柴火。最难熬的是冬天,雨雪天气多,但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、出门干活的外祖父能在临行前喝上一口热汤,仍然风雨无阻地去捡树叶。每当在冰天雪地发现一丛干草或干树叶时,母亲就像发现宝贝一样欢天喜地。 母亲经常说,自己就是个受累的命,结婚前每日在田间劳作,结婚后为了盖房子养孩子,更是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辛劳度日。甚至在我出生前的十几个小时,母亲还拖着臃肿的身子,在田地里辛苦地采棉花。 如今家庭条件改善许多,母亲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,这都是往日的苦日子让她养成的习惯,她知道生活的不易,所以从不奢侈浪费。 我随手捡起一片枯叶,遥想着旧时的那个少女捡起它时的快乐模样,心中有酸楚,也有温暖。 母亲曾温暖着一家人的生活,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,轮到我温暖您了,请您紧握我的手,让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日子。第二篇: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,只养活了我一个。那一年,农村闹瘟疫,一个月里,她死了三个孩子。爷爷对母亲说:“心里想不开,人就会疯。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!”后来,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,并常对家里人说:“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,你们不要管我。” 麦秋两季,母亲疯了似的劳动,每天鸡叫就到地里去,收割、打场,很晚才回到家里。她的身上都是土,头发上都是柴草,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。她的口号是:“争秋夺麦!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!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。”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。母亲把馍馍晾干了,再碾碎煮成糊喂我。我多病,每逢生病,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,祷告过往的神灵。母亲对人说:“我这个孩子,是不会孝顺的,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。” 家境小康以后,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之人,尽力周济。有两个远村的尼姑,每年麦秋收成后,总到我们家化缘。母亲除了给她们很多粮食,还常留她们食宿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,长得眉清目秀,冬天住在我家,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,夜里叫得很好听,我很想要。第二天清早,母亲告诉她,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。 一年春天,我从远方回来。母亲高兴得不知给我什么好。家里有一棵月季,父亲养了一春天,刚开了一朵大花,她折下就送给我了。父亲很心痛,母亲笑着说:“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,今天忽然开了呢,因为我的儿子回来,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!” 一九五六年,我在天津得了大病,要到外地去疗养。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,当我走出屋来,她站在廊子里,对我说:“别人病了往家里走,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!”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。我在外养病期间,母亲去世了,享年八十四岁。 蒋妍摘自《孙犁散文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第三篇:我的母亲 位于台中市大度山坡上的东海大学的右界,与一批穷老百姓隔着一条乾溪。从乾溪的对岸,经常进入到东海校园的,除了一群穷孩子以外,还有一位老婆婆,身材瘦小,皱纹满面,头上披着半麻半白的头发。清早进来,捡被人抛弃掉的破烂。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。第一次偶然相遇,使我蓦然一惊,不觉用眼向她注视;她却很自然地把一只手抬一抬,向我打招呼,我心里更感到一阵难过。以后每遇到一次,心里就难过一次。有一天忍不住向我的妻说:“三四十年来,我每遇见一个穷苦的婆婆时,便想到自己的母亲。却没有像现在所经常遇见的这位捡破烂的婆婆,她的神情仿佛有点和母亲相像,虽然母亲不曾捡过破烂。你清好一包不穿的衣服,找着机会送给她,借以减少我遇见她时所引起的内心痛苦。” 现在我一个人客居香港,旧历年的除夕,离着我的生日只有三天。不在这一比较寂静的时间,把我对自己母亲的记忆记一点出来,恐怕散在天南地北的自己的儿女,再不容易有机会了解自己生命所自来的根生土长的家庭,是怎么一回事。但现在所能记忆的,已经模糊到不及百分之一二了。 一 浠水县的徐姓,大概是在元末明初从江西搬来的。统计有清一代,全县共有二百八十多名举人,我们这一姓,便占了八十几个。我们这一支,又分为军、民两分(读入声),这大概是由明代的屯卫制而来。在界河的徐姓是民分,而我们则是军分。 军分的祖先便是“琂”祖。村子的老人们都传说,他是赤手成家,变成了大地主的人。因为太有钱,所以房子起得非常讲究,房子左右两边,还做有“八”字形的两个斜面照墙,这是当时老百姓不应当有的,因此曾吃过一场官司。 琂祖死后,便葬在后面山上。在风水家的口中,说山形像凤,所以我们的村子便称为凤形塆。琂祖有六个儿子,乡下称为“六房”,我们是属于第六房的。 大概在曾祖父的时候,由地主而没落下来,生活开始困难。祖父弟兄三人,伯祖读书是贡生,我的祖父和叔祖种田。祖父生子二人,我的父亲居长,读书,叔父种田。伯祖生三子,大伯读书,二伯和六叔种田。叔祖生二子,都种田。若以共产党所定的标准说,我们都应算是中农。但在一连四个村子,共约七八十户人家中,他们几乎都赶不上我们;因为他们有的是佃户,种出一百斤稻子,地主要收去六十斤到七十斤,大抵新地主较老地主更为残刻;有的连佃田也没有。在我记忆中,横直二三十里地方的人民,除了几家大小地主外,富农、中农占十分之一二,其余都是一年不能吃饱几个月的穷苦农民。 二 我母亲姓杨,娘家在离我家约十华里的杨家塆,塆子比我们大;但除一两家外,都是穷困的佃户。据母亲告诉我,外婆是“远乡人”,洪、杨破南京时,躲在水沟里,士兵用矛向沟里搜索,颈碰着矛子穿了一个洞,幸而不死,辗转逃难到杨家塆,和外公结了婚,生有四子二女;我母亲在兄弟姊妹行,通计是第二,在姊妹行单计是老大。我稍能记事的时候,早已没有外婆外公。四个舅父中,除三舅父出继,可称富农外,大舅二舅都是忠厚穷苦的佃农。小舅出外佣工,有很长一段时间,在下巴河闻姓大地主(闻一多弟兄们家里)家中当厨子。当时大地主家里所给工人的工钱,比社会上一般的工钱还要低,因为工人吃的伙食比较好些。 母亲生于同治八年,大我父亲两岁。婚后生三男二女:大姐缉熙,后来嫁给“姚儿坳”的姚家。大哥纪常,种田,以胃癌死于民国三十五年。细姐在十五六岁时夭折,弟弟孚观读书无成,改在家里种田。 三 父亲读书非常用功,20岁左右,因肺病而吐血,吐得很厉害;幸亏祖母的调护,得以不死。父亲一直在乡下教蒙馆,收入非常微薄。家中三十石田(我们乡间,能收稻子一百斤的,便称为一石),全靠叔父耕种,勉强维持最低生活。所以母亲结婚后,除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外,弄饭、养猪等不待说,还要以“纺线子”为副业,工作非常辛苦。她的性情耿直而忠厚。我生下后,样子长得很难看,鼻孔向上,即使不会看相的人,也知道这是一种穷相;据说,父亲开始不大喜欢我。加以自小爱哭爱赌气,很少过一般小孩子欢天喜地的日子。 到了十几岁时,二妈曾和我聊天:“你现在读书很乖,但小时太吵人了。你妈妈整天忙进忙出的,你总是一面哭,一面吊住妈妈上褂的衣角儿,也随着吊出吊进,把你妈妈的上褂角儿都吊坏了。我们在侧面看不过眼,和她说,这样的孩子也舍不得打一顿?但你妈总是站住摸摸你的头,依然不肯打。”真的,在我的记忆里,只挨过父亲的狠打,却从来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。 后来,叔父和父亲分了家。叔父分十五石田和一点可以种棉花的旱地,自种自吃,加上过继的弟弟,生活当然比未分时过得好。但我们这一家六口,姐姐十三四岁,哥哥十一二岁,细姐十岁左右,我五六岁。父亲“高了脚”,不能下田;妈妈和姐姐的脚,包得像圆锥子样,更不能下田;哥哥开始学“庄稼”,但只能当助手;我只能上山去砍点柴,有时放放牛,但牛是与他人合伙养的。所以这样一点田,每年非要请半工或月工,便耕种不出。年成好,一年收一千五百斤稻子,做成七百五十斤米,每年只能吃到十二月过年的时候;一过了年,便凭父亲教蒙馆的一点“学钱”,四处托人情买米。 学钱除了应付家里各种差使和零用外,只够买两个多月的粮食,所以要接上四月大麦成熟,总还差一个多月。大麦成熟后,抢着雇人插秧,不能不把大麦糊给雇来的人吃。大麦吃完后,接着吃小麦;小麦吃完后要接上早稻成熟,中间也要缺一个月左右的粮;这便靠母亲和大姐起五更睡半夜的“纺线子”,哥哥拿到离家八里的黄泥嘴小镇市去卖。在一个完全停滞而没落的社会中,农民想用劳力换回一点养命钱,那种艰难的情形,不是现在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。大姐能干,好强,不愿家中露出穷相,工作得更是拼命。 四 村落四围是山,柴火应当不成问题。但不是因我家没有山,所以缺柴火,而是因为一连几个村子,都是穷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数,种树固然想不到,连自然生长的杂木,也不断被穷孩子偷得干干净净。大家不要的,只有长成一堆一堆的“狗儿刺”及其他带刺的藤状小灌木。家里不仅经常断米,也经常断柴。母亲没有办法,便常常临时拿着刀子找这类的东西,砍回来应急;砍一次,手上就带一次血。烧起来因为刚砍下是湿的,所以半天烧不着,湿烟熏得母亲的眼泪直流。一直到后来买了两块山,我和父亲在山上种下些松树苗,才慢慢解决了烧的问题。分得的一点地,是用来种棉花和长豆角的。夏天开始摘长豆角,接上秋天捡棉花,都由母亲包办。有时我也想跟着去,母亲说“你做不了什么,反而讨厌”,不准我去。现在回想起来,在夏、秋的烈日下,闷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间,母亲是怕我受不了。我们常常望到母亲肩上背着一满篮的豆角和棉花,弯着背,用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,笃笃地走回来;走到大门口,把肩上的篮子向门蹬上一放,坐在大门口的一块踏脚石上,上褂汗得透湿,脸上一粒一粒的汗珠还继续流。当我们围上去时还笑嘻嘻地摸着我们的头,捡几条好的豆角给我们生吃。在我的记忆中,只有当我发脾气,大吵大闹,因而挨父亲一顿狠打时,母亲才向父亲生过气,却不曾因为这种生活而出过怨言,生过气。她生性乐观,似乎也从不曾为这种生活而发过愁。 五 辛亥革命那一年,我开始从父亲发蒙读书,父亲这年设馆在离家三里的白洋河东岳庙里。在发蒙以前,父亲看到我做事比同年的小孩子认真,例如一群孩子上山砍柴(实际是冬天砍枯了的茅草),大家总是先玩够了,再动手。我却心里挂着母亲,一股正经地砍;多了拿不动,便送给其他的孩子。放牛绝不让牛吃他人的一口禾稼,总要为牛找出一些好草来。又发现我有读书的天资,旁的孩子读《三字经》,背不上,我不知什么时候听了,一个字也不认识地代旁的孩子背。所以渐渐疼我起来。 这年三月,不知为什么,怎样也买不到米,结果买了两斗豌豆,一直煎豌豆汤当饭吃,走到路上,肚子里常常咕噜咕噜地响,反觉得很好玩。到了冬天,有一次吹着大北风,气候非常冷,我穿的一件棉袄,又薄又破了好几个大洞;走到青龙嘴上,实在受不了,便瞧着父亲在前面走远了,自己偷偷地溜了回来。但不肯把怕冷的情形说出口,只是倒在母亲怀里一言不发地赖着不去。母亲发现我这是第一次逃学,便哄着说:“儿好好读书,书读好后会发达起来要做官的。”我莫名其妙地最恨“要做官”的话,所以越发不肯去。母亲又说:“你父亲到学校后没有看到你,回来会打你一顿。”这才急了,要母亲送我一段路,终于去了。可是这次并没有挨打。父亲因为考了二三十年没有考到秀才,所以便有点做官迷,常常用做官来鼓励我;鼓励一次,便引起我一次心里极大的反感。母亲发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后,便再也不提这类的话。有时觉得父亲逼得我太紧了,所以她更不过问我读书的事情。过年过节,还帮我弄点小手脚,让我能多松一口气。 12岁我到县城住“高等小学”,每回家一次,走到塘角时,口里便叫着母亲,一直叫到家里,倒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;这种哭,是什么也不为的。15岁到武昌住省立第一师范,寒暑假回家,虽然不再哭,但一定要倒在母亲怀里嗲上半天的。大概直到民国十五年以后,才把这种情形给革命的气氛革掉了,而我已有二十多岁。我的幼儿帅军,常常和他的妈妈嗲得不像样子,使他的两个姐姐很生气;但我不太去理会,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时代。 以后我在外面的时候多,很难得有机会回到家里;即使回去一趟,也只住三五天便走了。一回到家,母亲便拉住我的手,要我陪着她坐。叔婶们向母亲开玩笑说,“你平时念秉常念得这厉害,现在回来了,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吧。”但母亲只是望着我默默地坐着,没有多少话和我说;而且在微笑中,神色总有点黯然。 六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,我由北平飞汉口,回到家里住了三四天。母亲一生的折磨,到了此时,生命的火光已所余无几;虽然没有病,已衰老得有时神智不清。我默默地挨着她一块儿坐着,母亲干枯的手拉着我的手,眼睛时时呆望着我的脸。这个罪孽深重的儿子,再也不会像从前样倒在她怀里,嗲着要她摸我的头,亲我的脸了。并且连在一块儿的默坐,也经常被亲友唤走。我本想隐居农村,过着多年梦想的种树养鱼的生活。但一回到农村,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,都是千疮百孔。而我双手空空,对他们,对自己,为安排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丝毫有所作为。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上的压力,只好又压着我奔向南京,以官为业。此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武昌住院了。我回到南京不久,哥哥死在武昌了,以大三分的利息借钱托友人代买棺材归葬故里,这对奄奄一息的母亲,当然是个大打击。此后,我带着妻子流亡。 (1970年3月《明报月刊》)
上一篇: 你应该知道勇敢是什么
下一篇: 此花开尽更无花
通用模板
推荐范文
范文 | 模板
- 王钦若写诗为吃肉 2022-05-11
- 真正的相爱,是彼此成全 2022-05-11
- 我高中的最后一小时 2022-05-11
- 授之以鱼,不如授之以渔 2022-05-11
常用 | 推荐
- 文明史与师道尊严 2022-05-11
- 郁达夫王映霞是这样把家毁掉的 2022-05-11
- 无人问我粥可温 2022-05-11
- 怨妇三千你独具一味 2022-05-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