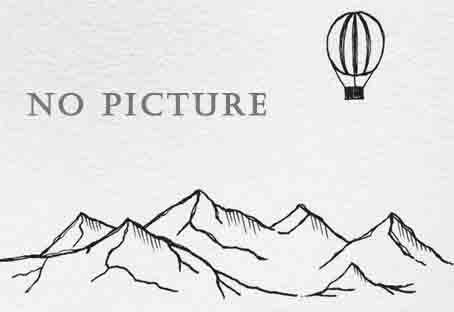游牧笔记
2022-05-08 14:12:50
无锡英才网
青海湖上 冷本才让坐在青海湖边的草地上。 他已经有87或者103岁了,反穿的那件羊皮袄使他看上去像一只羊。 冷本才让手里抱着一只酒瓶,瓶口里插着一根草秸杆。有时候他含住草秸杆嘬上一口酒,然后眺望海面;有时候他抓起一只羊骨头的朵拉(转经筒),诵念起来。 嘛。呢。叭。咪。哞。 他的眼屎挂住了脸面,嘴角上的白沫泛着干燥的渣粒和白光。他好像坐了有一个世纪多了。 更多的时候,他像石块,垒着。 他的羊在身后高高的山坡上吃青。青海湖边上是堆起的湟鱼的尸体。人们把六六六粉撒在草丛里灭鼠,雨水又把药粉冲进湖水,捉住了鱼群。 冷本才让坐着、喝着。 风从天堂般的水面上吹过,犹如心旌。 冷本这时候看见了湖面上一队华丽的马队,吹拉弹唱着从水面上走过。队中一辆亮丽的马车上是一个唐朝装束的女人,脸面像一只漂亮的母羊羔。 冷本每天都看见这队人马从水上走过。 恰好在日升中天。 冷本说,噢,那是文成公主的马队。她要入藏,和松赞干布大爷成亲。 像羔羊一样的女人呀。 冷本看到马队时,就要喝上一口酒——青稞酒在舌面上跑过,犹如草地上一筐子的鲜花在奔跑。 冷本是黎明出来的。 他坐着喝了整整一个世纪,等他回家时,两三瓶酒没有了。 夜晚的湖水也像草地一样。 星星们挤成一团,坐在破羊圈里。 冷本的家不远。一座泥坯的小房子卧在山冈上。冷本的院墙不是草泥糊的,而是一只只酒瓶垒起来的。瓶口向外,墩厚的瓶底把院子围得严严实实的。 羊圈也是瓶子围的。 羊不能吃亏。 一只羊要换几十瓶酒哩。 这个玻璃的院子,是冷本整整一个世纪喝下的。他有时不免骄傲。 冷本是个鳏夫。 夜里没事可干。羊们都安静地入睡了,青海湖上仿佛罂粟花般的香气吹来,沁人心脾。 青海湖上,酒瓶漂飞。 冷本喝着,诵着经。夜深了,他蹒跚着趴在围墙的酒瓶底上,朝外张望。夜光使酒瓶发出阵阵碎芒,酒瓶把微明聚拢起来,可以透视远处。 冷本望着水面。 他看见夜晚的青海湖面上,疾驶而过的一支马队。马队上的兵卒们手里高举着斧钺刀枪,胸前的圆圈里是一个大大的“兵”字。 长辫子飞动着。 马队估计有好几百万人,天天晚上都跑不到尽头。 冷本悄悄地喝酒,不敢弄出声响。 酒气像日光下沸腾的羊圈。 春天的一个夜晚,我去拜访冷本才让时,他偷偷地问我—— “康熙爷的队伍怎么还没完呢?他们是去唐古拉山里打雪豹吗?” 我说: “是的!” 复 仇 我和扎西、琼坐在草原深处喝酒。 草原远在一堆高入的寺庙和祭台深处,打马而过的人们,以及转经前往夏季牧场的部落与羊群,总会在这里盘桓数月,念经祈祷。 琼是扎西的新婚妻子。 我们三个,一块儿喝着土制的青稞酒。 一堆空酒瓶。 事实上,此刻透过窗子望出去,一面斜耸的山坡上毡帐如云。它们像一堆羊毛般的鸟群,模糊而杂乱。 夜幕四合时,窗下有传唱的声音。 我们是坐在一家回族的饭馆里喝酒吃肉。在高原,精于生意和吃苦的回族人,首推的生意是饮食。 黄焖羊肉。手抓饭。干炸羊腰子。 羊尾巴油。羊肋骨。清水羊杂碎。 屋外的高音喇叭里,一位藏族老人哀婉冗长的三弦弹唱声,使这顿饮食功课美不胜收。 灯光低悬着。 琼、扎西,和我。 我们三个在薄暗里喝酒吃肉。 但那个人终于找来了。 “呕……喳……,你一刻也不让我消闲,像狗一样地闻着找来哩。”扎西说。 “啊是!” “价,过来吃上些肉,别客气。酒,价你也喝些。”扎西又说。 “仇,还没报哩。” ——那个人站在灯影之上,肮脏的腰带上插着两把银饰的腰刀。手握在油光的羊骨头刀柄上,浑身酒气。 “价,先吃上些肉再说。”扎西道。 “仇呢?报过了再吃。” “颇烦着,颇烦着。我来了一个兰州的朋友,不容易价。我和我的朋友喝个酒,你就来颇烦我着。” “我,心里也颇烦着。” “价,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是兰州来的诗人叶舟,我的,朋友。” “价,没听说过着。” “我的朋友在哩。价,我陪着喝个酒,你价一个劲地颇烦着。” “仇,先报过。” “颇烦着,颇烦着。价,这个仇把我的酒,和我的朋友干扰着。心里嘛,价要落下个病根根的哩。” “仇要来哩,不是我要来哩。” “价,我倡议一下,你把我的媳妇子领去。价,你俩个去报仇去。我要好……好好地和我的朋友喝上一下子。” “成!” 窗下响起了一阵杂沓的傲慢蹄声,由近及远,几至模糊不清。琼在下土楼梯的时候,对我咧嘴笑了一下子。她的笑声仿佛在说,那一碟子手抓羊肉凉了,再蒸热了吃。 扎西继续和我喝酒。 扎西边喝酒,边和我说起他打猎的事情——后来我才搞明白,他的那些打猎的历险故事,其实不过是在黎明时分,在公路上扛回来一具具夜间被飞驰的卡车撞死的动物。有些还是国家严令禁捕的珍稀动物,但它们是被汽车撞死的,就该闭嘴。 一地的空酒瓶子了。 扎西还要喝。打烊的哥哥单腿睡在隔壁的一根条凳上,呼呼作响。 夜幕下,那老人弹唱的是《格萨尔》片断。 那个复仇的人又来了。琼没来。 他站着,不吭声。 “仇,报过了没有?”扎西问。 “她喝醉了,像一只乖母羊。” “颇烦着!价,我和我的朋友喝个酒嘛,价有人颇烦着哪!” “仇,报过了再喝。” “价,这么办吧,我觉得颇烦了。” 扎西从屁股后面,抽出了一把锋利的藏刀,捋下袖子,在自己的胳膊上哗哗哗地拉了三道口子。 血喷地一下涌了出来。 “颇烦着。价,我的朋友心里落下个病根根了,酒没喝好着。”扎西说。 “仇报过了,算了。” 复仇的人依然立在灯影之上,这使盘腿坐在炕桌前的我看不清他的脸。他站了一会儿,喉咙里嘟哝了些什么。 扑腾一声,他也盘腿坐了下来。 他用牙咬开了一瓶酒的封口,嘟嘟嘟地喝了起来。末了,他也抽出刀,像扎西那样,在胳膊上割了起来。 但他只割了一道口子。 随后,他举起一扇羊肋排,兀自啃吃起来,边嚼,边和我与扎西碰杯。 酒瓶发出刀子断裂的声音。 他叫尕藏。 尕藏说:“颇烦着,颇烦着。不报么,仇要找来哩;报么,好朋友在这里坐着哩。价,让人颇烦着!” 三个人喝至天亮,梦见佛光。 婚 礼 尕旦和我骑马走进了草原深处。这是秋天的日子。天空粗糙,大地雍容,鹰在疾驰,马背上披着锦绣斑斓的被面,在日光下反射着斑点。草原辽阔,在绿色的毡毯上,那几幅彩色的被面很夸张,也很耀眼,据说那是杭州的丝绸做成的。它们是送给才旦的新婚礼物。 才旦是一个酒鬼、一个草原的好骑手、三个孩子的父亲。他还是我和尕旦的朋友。 这样说的意思是,我和尕旦其实也是酒鬼。两个月前,我接到了才旦捎到兰州的话,说他要和那个狐狸长相的女人结婚了,要我到草原深处和他好好喝一杯。我爽快地答应了。我先是坐了三天的长途班车,最后雇了一辆三马子才找到了尕旦。我们换上了两匹大马,在起伏的山峦上走了八天。 秋天明净地在草原上奔驰,我们好像迷失了方向。方向是才旦指的,可他现在已经烂醉如泥,歪歪斜斜地耷拉在马背上了。他早就醉了。他的怀里,仍旧戳着几只青稞酒的瓶子。走马散漫地徜徉在草原上,他也散漫地捏住瓶子往嘴里浇灌。他像一个消防队员。他一直在浇灌着自己。 大鹰在头顶徘徊,像一把匕首搁在天上,明晃晃地发光。马蹄惊起了几只蝴蝶,像光斑一样闪烁。它们落在了锦绣斑斓的被面上,误以为那是一束束鲜花呢。 尕旦嘟哝说:“喔,一个酒鬼要改邪归正了,一个酒鬼要放下酒罐子立地成佛,一个酒鬼在这个秋天给自己一些想头了。你会相信吗?”我纠正说:“他都让那个狐狸长相的女人生了三个娃娃了,他非要娶她啊。否则,他能算一个好酒鬼么!” 远处的山冈上,经幡在飞。煨桑的淡蓝色烟雾,在天空中慢慢洇开。尕旦和我已经迟到了好几天,可我们并没有把鞭子撂在马背上。马是无辜的。 草原上的婚礼一般要进行十几天,大家白天围在锅灶边吃肉喝酒,晚上则会围着一堆篝火跳锅庄。在黯淡的夜空下,那些女人们身上的银饰就会发出丁冬的响声,这说明她们跳到了兴头上,而男人们会无一例外地醉倒在帐篷周围。 竟然,翻过第九座山冈时,我看见才旦坐在一堆麻尼石旁边。他的面前是一块绣花的毛毡。毡上摆放着香炉、肉疙瘩、银碗和一把刀子。才旦好像是在等谁,见到我们的时候他一脸的茫然。他举手,做了一个朝拜的动作。很显然,他已经烂醉如泥了。 可他还是对我笑了一下,伸手把我抱下了马背,替我掸了掸身上的灰尘。他撕下了一小块干肉,喂进我的嘴里;又从一只皮囊中挖出来一小撮酥油,抹在了我的脸颊上;最后,他干脆把一银碗青稞酒端给我,要我一饮而尽。 没有退路了,我接过来,径自灌进了自己的胃里。 我对才旦说了一些祝福之类的话。他根本就没听进去,又给我盛了一碗,命令我一饮而尽。酒像一股火焰,跑进了我的身体内。我在一瞬间被点燃了。我把几块被面披在了才旦的身上,又对他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幸福话。孰料,才旦却用手阻止住我,样子很满足地说: “现在么,我们公平了。你看你一下子就喝大了,你的酒量这么差劲了,你这样喝大了,你才不会糟蹋我,你就不会再笑话我了呀。” 才旦又说:“我在这里,堵了你们几天几夜了。你们终于来了哦!” 清晨的太阳照在石崖上, 红石崖如屹立的神像, 那是佛一样的客人到来的象征。 才旦一边唱着迎亲的曲子,一边拿起青稞粒和五谷杂粮,撒向天空。这时候,尕旦从马上一头栽了下来,仿佛一只凌乱的麻袋砸在了地上,很不争气。我本来想上前扶一下尕旦,可我浑身像一团棉花那样柔软不堪。日光太亮了,地上逶迤而来的酒气,让草原变成了一座沸腾的马圈。我一软,就跌倒在了一堆青草上。尕旦和我,像两只打开的麻袋那样横陈于草丛中,知觉全无。 我们睡了有三天三夜。 才旦在我们酣睡的时候,独自一人坐在那一方毡毯上喝酒。他边吃着酒肉,边醉眼迷离地唠叨说:“你是我的朋友,你那么老远来参加我的婚礼,我心里过意不去得很呀,我自罚上三碗吧!我一定要自罚上三碗,你们别劝我呀!” 我和尕旦谁也没劝他,一任他像草丛下的溪流那样,茫无目的地流淌。 我们睡了有三天三夜。才旦自罚了三天三夜。 最后,尕旦、才旦和我好比三堆未点燃的粪火,一直沉默了有三天。而那三天,在草原深处的帐篷群里,一场火热的藏族婚礼正如火如荼地展开,就连机灵的藏獒,也没有嗅出我们的一丝踪迹来。 三个神秘的酒鬼,让草原深处挂念不已。 打猎的故事 喂,你想打猎吗?你想扛回去一匹唐古拉山里的雪豹吗?呵呵,那你跟我到动物园去! 夜晚的星星们,像一包袱突然抖露出来的玛瑙,从那曲的天空中照耀过来。其实,那不是星星们发出的光,而是雪山反射过来的透明的夜色。仁青扶着我走出了一家酒馆,步履踉跄地呕吐着。 他身上藏式服饰的图案中就有一块豹皮。那些神秘的花纹可能启发了他。于是,他邀请我到动物园里去打猎。 那曲那边的草原上,正在举办“恰青”大会,整个藏北的帐篷们都游移向那曲。这个小城里似乎只剩下了仁青一人。他没理由不喝大呀。我们走在狭窄的街道上张望了半天。后来我们索性互相搀扶着,大声唱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谣曲,往动物园的方向挺进。 仁青说:“其实,我不是那个叫仁青的人,我只不过假装了一回仁青罢了。我的前世是一个牧羊人,那时候,我才13岁,你信不信?有一天,我赶着羊群钻进了唐古拉的一个山沟里,羊们在山上吃青,我在一个山洞里睡着了,我还做了一个漫长的梦,我梦见一位佛爷站在天上教我说书,我背诵了几天几夜,等醒来以后我一张嘴,我就能说出全本的《格萨尔传》了,可那时候我连一个字母也不认识呀。” 我说:“我信你。” 我们一直走到了动物园的后门,在星光下翻墙而入。 ——夜晚的动物园里阒寂无人。在漆黑的深处,偶尔会传来野生动物们低低的喘息声。一只高寒地带上的蝙蝠在空中飞行,它的翅膀差一点儿刮在了我的脸颊上,吓我一跳。 仁青蹒跚地往前走,绕过几个黑乎乎的低矮建筑,来到了雪豹的笼子前。 几只蓝得让人忧伤的眼睛,在笼子里晃动不已,披着夜色的雪豹此刻比夜色更黑,鼻孔里喷出的白汽逶迤上升,四周围传来雪豹柔软的脚步声。 仁青对雪豹问候说:“乔带帽(你好)!” 在晴朗的星光下,我看见仁青从袍子里摸出了一枚银子的挖耳勺。他踉跄地走到了铁笼子前,轻轻一下,那扇铁门奇迹般地被打开了。 仁青钻了进去。 他的身影和那群雪豹混为一团,漆黑一片。 过了好久,在我惊魂未定时,仁青突然站在铁笼子里,双手抓着粗大的铁栅栏,对我嘿嘿嘿地发笑。他招了招手,似乎是在对我发出邀请。 那些凶猛的食肉动物居然匍匐在仁青的脚下,挤眉弄眼,哑巴似的。 仁青说:“我和你一起打猎呀,你说的!” 我想,我的无动于衷可能惹怒了仁青,他伸手对我做了一个鄙视的手势,那意思好像我是一个天生的胆小鬼。 可我真不愿意糟蹋自己。我坦白吧,我是一个俗人,我不能把自己当成雪豹的一块点心啊。我准备起身,我打定主意要跑到有饲养员的地方,请求他们帮助把仁青从铁笼子里解救出来,除此之外,我束手无策。他是我的朋友,他现在喝大了,他会为喝大而丢了自己的性命的。 这时刻,仁青却突然开口说话了。 仁青以一种极其鄙夷的口吻说:“你不是我的朋友,兰州来的叶舟才是我的朋友,我亏欠下他的人情了,那一次我没好好招呼他,让他一肚子的委屈,我没邀请他打猎,可我现在邀请你了,你怎么能不替我的朋友叶舟扛回一匹豹子呢?” 说完,他一头栽倒在地上。 那些豹子,竟然像铺盖卷一样依偎在他周围,为他取暖。 他一直睡到了次日黎明。 他在凛冽的天光中揉了揉眼睛,在铁笼子里翻身而起。他走出了雪豹的领地,还给它们说了些什么,我没听清。出了门,仁青看见在铁笼子外满眼焦急、困倦缠身的我后,猛地一愣怔,嘴巴能塞下去一只拳头。他大言不惭地对我说:“嘿!叶舟老哥,你怎么在动物园里呀,你是从兰州来看我的吧?!” 我扭头看了看铁笼子里丢三落四的几只玻璃酒瓶子,又看了看仁青明显瘪下去的胸襟,就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 我对仁青说: “对呀,我刚刚下了长途班车,来找你的!”
通用模板
推荐范文
范文 | 模板
- 王钦若写诗为吃肉 2022-05-11
- 真正的相爱,是彼此成全 2022-05-11
- 我高中的最后一小时 2022-05-11
- 授之以鱼,不如授之以渔 2022-05-11
常用 | 推荐
- 文明史与师道尊严 2022-05-11
- 郁达夫王映霞是这样把家毁掉的 2022-05-11
- 无人问我粥可温 2022-05-11
- 怨妇三千你独具一味 2022-05-11